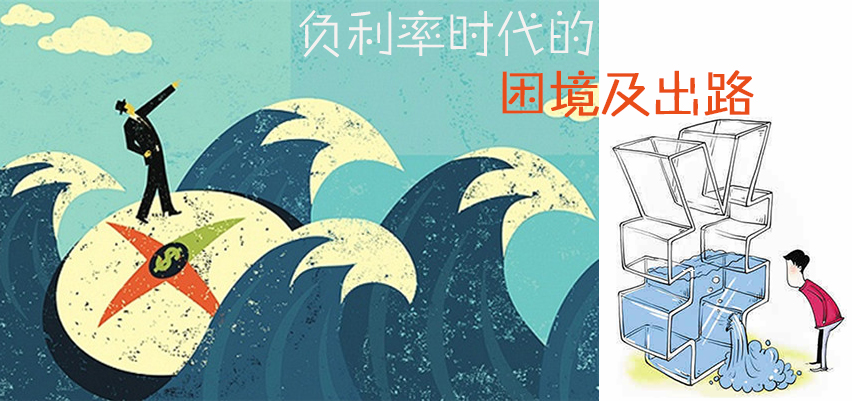洪永淼:追求“止于至善”的科学精神
- A-A+
- 第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 2010-12-20 11:01:26 来源: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记者站 作者:佚名 0
记者: 乔雅君,费玉新,冯秋月
采访时间:2010年11月21日上午十点半
采访地点:河南省黄河迎宾馆
记者:洪老师,您好!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对您进行采访。您曾经谈到“计量经济学所面临的局限性不是计量经济学本身所特有的,而是整个经济学科所面临的局限性。” 您能具体谈谈这一观点吗?
洪永淼教授:从整个经济学科的特点来看,其假设条件一般是没有办法直接去验证的。其实过去好几代经济学家一直想要让经济学成为一门像物理学这样的科学。那么什么是科学呢?首先就是理论体系要有逻辑性,从假设到理论本身,到推论,一定都要有逻辑性,不能有逻辑错误。更重要的一点是,你的理论能不能解释现实,也就是说理论跟现实要有一致性。而后面这一点其实就是计量经济学的工作。我们现在发展一整套的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模型和工具,其实都是为了用来分析经济数据,然后看看这些经济数据跟理论是不是相吻合。那么为什么说计量经济学或者整个经济学科有局限性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在自然科学里面,像物理、化学,或者生物,这些都是可以做实验的。你之前可能做了大量的实验来验证某种假说,然后提出了你的理论。等你的理论提出之后,其他人在你的假设条件下可以独立进行实验,来验证你的理论。但是经济学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例如研究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转型问题,别人是不可能让中国经济回到三十年前再重复来实验一次的,这种实验是没有办法做的。虽然现在也有实验经济学,但是毕竟实验经济学研究的领域相对还是狭窄的,对于大多数经济现象,我们都是被动的观测者,并不能主动去产生数据。因此,如果你现在通过实证研究提出了一个观点,但别人想要通过做实验来验证这个结论是不可能的。在物理学、生物学上,我们可以靠做实验来判断对错和真假;而在经济学方面,只能是看你使用的分析方法,如果是实证研究的话,就是看你的计量经济学方法,看哪一个更一般、哪一个更具有科学性,只有这样,才能够判断出哪种结论要更好一些。而这也是相对的。就是说,也许现在受到数据的限制,或者所使用的经验的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不够好,不能把目前的理论推翻掉,但这并不一定说明这个理论就是正确的理论;过了一段时间,经济现象的数据多了,方法完善了,可能就可以把这个理论推翻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其实是有一点怀疑,经济学是不是可以达到像自然科学那样比较完美、或者完善的程度。所以我们只能从多方面着手,让经济学在方法上、在各方面能够尽量往科学研究方面靠,但是真正要达到自然科学的那种水平还是相当困难的。这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最重要的一点区别。
记者:虽然目前在国内财经类高校的本科教学中非常强调《计量经济学》课程的重要性,但一方面学生学起来比较吃力,另一方面学生学过之后又不容易很快看到这门课程的用处,因此很多本科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学这么难的一门课程到底有没有用?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洪永淼教授:我1987年在人民大学参加一个经济学培训中心,当时请的都是美国的一些教授来讲课,我们看的都直接是国外一些学术期刊上的文章。结果看不懂,我当时就问了一位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我到底要花多长时间才能看懂这些学术论文?他的回答是:五年。等到很多年以后,我在美国读完博士、工作以后,有一天我突然醒悟过来,他讲的五年正好是美国的博士的学制,他的意思是,当你通过博士期间的训练以后,也就是大概需要五年的时间你才能够看懂你本专业的学术论文。这说明,想要掌握计量经济学并达到能够应用的程度,的确是要花费一些时间的。另外,对于中国的一些学生,在学了数学、计量经济学这样一些课程以后不知道怎么用,我觉得这本身跟中国的一些课程的设置是有关系的。在美国,在你学习经济学之前就会告诉你一些必须的先修课程,比如在上中级微观之前就会告诉学生你必须先学习微积分,因为中级微观里要学到效用最大化等问题,就要用到数学里的求极值的方法,就要用到微积分的知识。这样就给了学生一种导向:要想修中级微观,就要先学会微积分;而且,这样还可以告诉学生微积分是怎么样用在经济学的分析里的。而在中国目前的课程设置情况下,学生在学习高等数学的时候是看不到以后这些课程将会用到哪里的,学的数学课程和以后所学的经济学里的数学应用是有些脱钩的。再者,学生之所以觉得数学和计量经济学比较难学,那可能跟中国目前的教学文化也有一定的关系。现代经济学之所以要用到数学、计量经济学等工具,就是因为现代经济学是建立在一套很严谨的术语、规范的基础之上的,有着一套很严谨的逻辑框架,因此它的内容和形式是高度统一的。你为了分析一些高深的经济学问题,就必须使用一些复杂的数学工具才能实现。当然,我觉得国内的数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老师们的教学水平在某些方面也要有一定的加强。由于计量经济学要求的门槛高一些,特别是对数学工具的要求比较高,我们就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数学工具上,而忽略其背后的经济含义。如果老师们能够把这些经济含义通过一些例子讲进去的话,我相信学生肯定会喜欢计量经济学这门课的。
记者:计量经济学作为一种方法论,目前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使用。但同时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您是怎么看待这些批评的?
洪永淼教授:我觉得数量分析方法的广泛应用是一种进步。看看中国经济学教育,在1980年之前的30年,经济管理类的学生是不用学数学的,他们主要就是学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而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就是marginal revolution,就是边际革命。所谓边际,对应的数学就是求导数,所以经济学里使用数量分析方法就很正常。为什么要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去做呢?先看看国外的情况吧。美国高校里的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一共有三类:第一类是理论研究,具体分为微观理论、宏观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理论三个主流学科;第二类是应用研究,就是实证,就是用数据来描述客观经济现象,不加任何价值判断;第三类就是政策性的,而政策性的研究在好的高校的经济系里面一般是很少的,是不提倡的。不过这在中国可能正好是倒过来的。中国这种纯学术的研究本身就比较少,比较早期的一些经济学研究都是带有价值判断的,例如批判马歇尔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叫庸俗经济学。后来在接触西方经济学之后,国内学者才懂得必须做实证,就是要以事实为依据,只描述整个经济过程,不加任何价值判断,读者看了以后自己会去判断。这个实际上是社会科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论。一百多年前,在德国有两个学者争论了半天,后来达成了学术界的一个共识,就是科学的研究方法最好不要带任何价值判断,客观地描述整个过程就可以了,这样才可能真正地把一些真相、真理发现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在经济学里,你不跟数据打交道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经济现象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分析的工具也应该相应地变得复杂才对。我很难想象,复杂的经济现象照样还可以用最简单的一些分析方法来做,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在中国有很多政策性的建议,它们都是建立在跟数据不打交道的经济逻辑思维上的,而这种经济逻辑思维是隐含的有前提的。如果你的前提错了,你的逻辑思维即使正确,你得到的结论也可能和经济现实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经验验证,也就是为什么需要统计、计量的分析。因为经济系统没有办法做实验,因此想要判断一个结论的科学性,每个人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如果没有计量分析,就会出现一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结果,就很难达到共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现在在国外的经济研究,我估计80%以上的研究都是实证研究。可是,目前中国的一些学者,包括一些年轻学者,在不是很懂计量经济学方法的时候就拿来用,比较机械地照搬别人的方法,这样可能就会得出和中国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的结论。而这些就给了那些批评的声音以借口,说用计量经济学方法预测的不准确、分析的与现实不一致等等。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数量分析方法就是错的。本身这就是一个必经的阶段,现在我们看到的国内的很多学者使用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是跟“练习”差不多的。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即使当这些方法掌握之后,分析中国问题时还要具体考虑中国的时空等条件。我相信,到那个时候,批评的声音会少一些。
记者:由于时间和精力总是有限的,在您的个人学术研究与从事行政工作之间可能会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冲突,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的?
洪永淼教授:在美国,系主任基本都是轮流做,因为没人愿意做。国外学术界的评价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你的学术成果,基本上就是以你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作为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担任行政的职务,你大概就没时间去做研究了,因为像我们在国外写一篇文章,大概要花三年的时间才能够发表出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担任任何的行政工作对你个人的回报率是非常低的。如果你当的时间比较长的话,甚至可能你跟踪你本领域的学术前沿的能力都要差一大截,因为国外的研究人员一批批涌现出来,更新换代特别快。在中国,这个环境是不太一样的。在美国,你当一个系主任或者研究院的院长,你要去改变美国的学术环境是比较困难的;而在中国,如果把国外的一些方法或者实践拿回来用的话,可能在国内会带来相当明显的变化。因此,如果在中国办教育,可能会带来不同于学术方面的另一种成就感,也就是说,除了学术以外,可以实现你的教育、教学的一些理念。像过去五年我们在厦门大学的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做的很多事情,在美国其实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在国内,这样一些稍微的改变,产生的效果就非常明显。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国外的核心课程,比如一星期四节课,这四节课一定要分作两天来上,而且这两天还不能是挨着的两天,一定要分开,比如星期一和星期三,或者星期二和星期四,就是要给学生消化知识的过程。而在中国,有些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课程,常常是一个上午、一个下午或者一个晚上就把一个星期的课上完。为什么这样不好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经济学里有一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厦大我们就规定四节课一定要分开上,不准把四节课放在一起上。以前我们有一个青年老师跟我说,上同样一门课,在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比在其它学校上一个学期他多备了三分之一的课量。也就是说,仅仅是把四节课分两天上这样一个小小的变化,学生就多学了三分之一的东西。可以看出,在国内稍微一点变化,就可能产生很明显的效果。我觉得中国的学生都很聪明,不会比美国一些最好的学校的学生差,但是由于教育制度的一些问题,培养出来的学生可能国际竞争力稍微差一些,或者没有办法马上去从事研究。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感觉到有很事情可以去做。当然这些都会影响到我自己个人的学术研究,但是这些事情虽然会占用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也同时实践了我自己的教学理念,也会带来很大的成就感,这和个人的偏好和职业目标是有关系的。目前中国制度还不完善,各方面的环境还有很多改善的空间,因此在这上面的投入会产生很大的工作上的成就感。不过,不管怎么样,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不行的,要靠一批这样的人才能完成,既要有国外回来的,也要有国内的人,要形成一种氛围才行。
记者:据说您非常喜欢厦门大学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中的“止于至善”四个字,那“止于至善”是不是意味着一种追求完美的人生目标?
洪永淼教授:我觉得“止于至善”其实是一种科学精神。“自强不息”可能在全国很多大学的校训里都会有,而“止于至善”却用得很少。这四个字是从诗经里借用过来的,是由陈嘉庚和第二任校长林文庆共同提出来的。有人说厦大是全国最漂亮的校园,不过这个对我一点吸引力也没有。学校漂亮当然好,能够让你心情舒畅,但这些对你提高教学质量、提高研究水平没有必然的联系。我觉得一个学校最重要的是他的科学精神和学术氛围,而“止于至善”的境界就体现了陈嘉庚作为创立厦大的“校主”当初的远见。除了这四个字以外,厦大有一个非常大的运动场,我们叫“上弦场”,操场是半月形的,这就包含了中国的古训在里面,就是不能是圆形,圆形就满了,半月形就是让你要虚心。厦大已经有九十年的历史了,他让我感受最深的是这一些。我们自己在做研究的时候,我的感受也非常深刻。在国外的比较严谨的经济学研究里面,比如说数学证明,你需要一步步地去推敲、去验证。作为一个学者,每一步都必须求真、求实,每一步都要踏踏实实。在这个时候,你不能够有一种侥幸心理,以为自己能够混过去或者忽悠过去,那样对一个学者的学术生命伤害会非常大。当然,“止于至善”的追求未必是经济学里一种“理性”的选择。经济学里有所谓的效益成本分析,但当你追求完美的时候花费的力气总是特别地大,好像这种做法并不符合效益成本分析的原则。但我感觉这正好就是一种对人生、对学术研究的态度,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点。
记者:如果把“止于至善”作为人生目标的话,您这一生一定将会过的非常累,在您得到很多东西的同时,也一定会失去很多东西。您是怎样看待这种得失的?
洪永淼教授: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周末有时候到一些老乡家里去玩,看见他们全家或者朋友聚在一起看电视休息聊天,我当时是很羡慕他们的生活,我作为一个学生,这种时间基本上是没有的。所以我一直有一种梦想,是不是能够努力一段时间以后,可以好好享受一下这种乐趣。可是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没有找到这样的时间。所以我感觉就跟经济学一样,当你的资源有限的时候,你必须选择,不能面面俱到,就是要选择那些对你最有用的事情去做。如果每样都想选的话,结果是每样都做不好。那这样会不会有缺陷呢?我觉得会有。但是更重要的是,当你集中力量去做一件事的时候,那种带来的成就感会远远地弥补你在其它方面的缺憾。这个就是跟一个人的人生观、对生活和事业的态度是有关系的。每个人的效用函数都不一样,所以他们的选择就可能会不一样。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我最迷茫或者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就是刚考上物理的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当时一直不知道以后干什么,因为我看见我的物理老师白发苍苍在地下室做实验,我感觉这样过一辈子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后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厦大经济学院的第一任院长葛家澍,他在80年代的时候允许理科的学生转到经济学去,我就是那个机会考到人民大学的经济学培训中心,我在那里是第一次接触经济学的东西。学了一年之后回到厦大,我继续学习了一门西方经济学说史,由于研究的时候要带着价值判断,要去批判一些东西,所以我当时又有些后悔,觉得不应该转到经济学这方面来。后来,我硕士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当时是1988年,是中国通货膨胀最高的一段时期,所以当时出去的目标是要读货币银行。而到美国一年之后,我终于发现我真正感兴趣的、能够发挥自己一些数理背景特长的,就是计量经济学。自从我选了计量经济学之后,我就全身心投入这方面的研究了。当时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很懂,有时候一篇paper要看一两个星期才可以看懂,这个过程确实非常痛苦。但是因为对这个领域感兴趣,对这个专业感兴趣,所以在我读博士的时候、甚至工作以后,虽然每天晚上都要到凌晨一两点钟才睡觉,看上去似乎是一种很痛苦的生活,不过在精神上我从来没有觉得压力很大,或者很痛苦过。当你的文章发表出来的时候,你看到了成果,你会觉得以前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讲,一个人,不论你将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一定要选一个你最感兴趣的东西,而不能随大流,不要看哪个专业比较热门,那个可能不是你的长处、也不是你的兴趣。
记者:一些年轻学者或者学生可能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缺乏吃苦的精神,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洪永淼教授:说到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吃苦,我觉得这跟中国目前的环境有关。经济学里有一句话,NO FREE LUNCH,就是说,你没有一定的投入,你想要有产出是不可能的。在中国,这跟你的家庭条件和社会背景是有关系的,有一个好的爸爸妈妈,可能会帮到你;在国外,制度是比较公正的,投入和产出是成正比的,有多少投入,才有多少产出。在这种制度下,在这种氛围下,如果你的目标定的比较高,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艰苦奋斗的准备,一个人的成就和他的努力程度以及他的个性都是非常密切相关的,这是我这些年来通过自身的经历以及身边很多的例子得到的感受。
本文稿根据对洪永淼教授的采访录音整理而成,未经洪永淼教授本人审阅。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2022年预聘教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是以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毕业的马寅初学长命名的一所与国际接轨、高起点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招聘事业编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招聘事业编制研究员2名。北大汇丰智库研究实习岗位招聘启事
北大汇丰智库将于2020年起招聘实习研究专员若干名。
-
全球经济逐渐回暖
232人看过
-
马修. 斯劳特:中国、知识产权与美国就业
99人看过
-
宝洁:致命的自负
232人看过
-
投行的春秋战国:并购定天下
381人看过
-
2015:经济学家还会打起来吗?
204人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