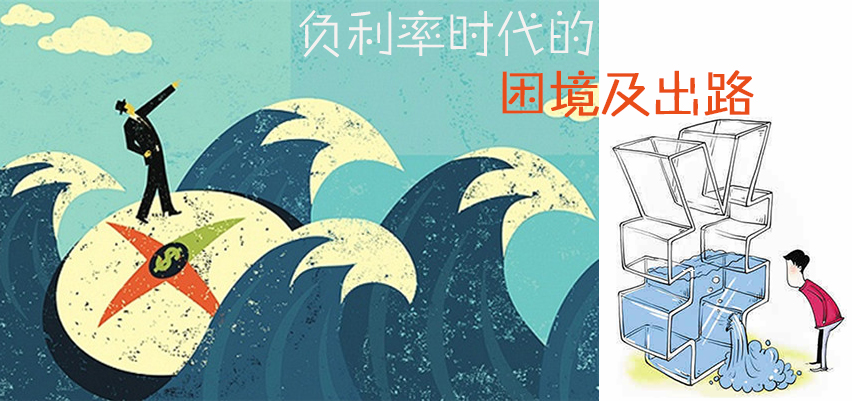雷鼎鸣教授谈经济学教育
- A-A+
- 第六届中国经济学年会 2006-12-21 00:00:00 来源: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作者: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黄晓晖 薛世坤 0
雷鼎鸣教授个人简介:
雷鼎鸣教授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雷鼎鸣教授现担任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及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于1984-1993年担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经济系副教授;1987年任大连工学院工业科技管理全国培训中心美方教学团成员;1999年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雷教授参加的部份专业活动有:美国经济学会会员,计量经济学会会员,中国经济学会(国外)会员,北美州中国经济学会会员。廿四份国际专业经济学报审稿人,剑桥大学出版社审稿人,香港研究资助局评审人,发展地区学报编辑顾问。担任的部份公职及公共事务有:香港特区政府长远房屋策略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区政府就业专责小组成员、香港特区政府强制性公积金上诉委员会成员、香港电台电视部顾问团成员、长江开发沪港促进会专家小组成员、香港中华厂商会经济小组顾问、香港清水湾学校校董会成员、科技大学顾问委员会成员。
雷教授近年所获荣誉包括:第二届全球杰出华人暨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1999)、奥地利萨尔斯堡研讨院费利曼院士(2000, 2003)、国际商学院荣誉组织Beta Gamma Sigma科大分会主席。
雷教授曾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多篇专业著作,其中三篇被选入“经济学关键性著作国际文献馆”,并著有《论港元危机》、《用经济学做眼睛》、《风眼中的经济学》等七本书。
记者:雷教授,您好!我们是武汉大学经管院的本科生志愿者,是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的特邀记者,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雷教授这是第一次来武汉大学吗?可否谈谈对这次年会的看法或最初印象?
雷鼎鸣教授:对,这是第一趟来武大。我这是第二次参加中国经济学年会,去年在厦门大学。我来的原因主要是要多了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速度和现在的水平,但是光看这两次很难作出具体的比较。我感觉中国现在的经济学跟十年前、五年前的经济学相比,显然有进步,从这次和上次(年会)都可以看出,论文的技术水平比从前是提高了。但是还存在不足。除了一些很有经验的学者所做出的研究以外,其它一些文章中的经济学思想还是不太够。技术是进步了,用的数学知识都是相当不错了,但是得到的结果对经济学有多大的贡献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有提高的余地。有些理论研究是不是和前人所做过的工作重复了?还有,很多学者都会看到这个问题:研究的前沿到底在什么地方?什么问题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还需要一段时间,水平才会慢慢提高。中国的经济学者还要多读国际上的一流研究文章。在某一个领域中是不是做得很好、很彻底?得出的结果意义有多大?值得提出疑问。反而,在中国经济研究方面,用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数据,倒是没有刚才所说的对经济研究前沿掌握不了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新的,很难重复研究。
记者:一代经济学宗师Milton•Friedman生前曾批评香港的学券制设限,认为让家长选择按政府路线办学的非牟利幼稚园是不智的做法。请问您怎么看待他的评价?
雷鼎鸣教授:Milton•Friedman的批评其实很有道理。Milton•Friedman他本人也很明白,香港的经济在最近的10到20年来,也不能完全地说是自由经济。因为从90年代初开始,不是说从97年开始,政府的干预多了许多,而且香港的工商业很多也都不是自由竞争,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垄断。
不过香港的经济有几点很符合自由经济,是很值得注意的。第一条是香港基本上没有关税。除了少量的商品,如汽车、烟、酒以外,香港的进出口基本上都是零关税。第二条,香港政府的开支占GDP的比例不算太高。香港政府的规模——占GDP的比例大概是18%到20%左右。因为香港没有军费,也没有所谓政府给的退休保障的福利,所以相对来说,香港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其实不算非常低。但是跟那些高达50%、60%以上的欧洲国家相比,香港的18%、19%算是比较低的了。根据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Robert•Barro的研究结果,政府的规模越大,对经济长期的增长越不利。原因很简单,政府用的钱是纳税人的,所以它没有谨慎的去花费这些钱。当然, Barro、Friedman,包括我自己,都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政府是要有的,但是差不多所有的政府都超过了最优规模。香港现在18%、19%的比例还算可以,我希望更低。在80年代后期,最低的时候是14%、15%,后来90年代初开始,一直在增加,最高的时候达到22%,可见政府规模的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快50%左右。增加政府的开支以后,的确有很多浪费。所以Milton•Friedman也看到了香港政府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
Milton•Friedman还说香港“自由经济”的招牌已经没有过去那么闪亮了。我也同意这个看法。我们看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很多时候不是看政府开支,还有很多政策方面的考虑。从97年以后,香港政府有好几个重要的直接干预经济的政策,但是都没有得到有效的结果。举个例子,香港在1999年提议建迪士尼乐园的时候,政府拿出一大盘数据,说投资回报会如何高。当时我们看到这些数据都很怀疑,因为迪士尼在世界潮流上已经走下坡了,受欢迎的程度很难说。到去年建好以后,负面的消息不断传出。反而香港传统的游乐场,像海洋公园,有些时候比迪士尼的表现还要好。从最近的数据来看,对于迪士尼项目,政府的投资部分回报肯定不会很高,迪士尼对社会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还有,香港政府要搞高科技,搞数码港,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挺失败的例子。很多东西出发点都是很好的:补贴、工业政策,但是从香港的例子来看,到后来没有很好的结果。所有出现的这些例子很符合Milton•Friedman说的“政府的干预多了,导致不好的结果”。
记者:从2005年7月起,您联同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引进了一种新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进行预测。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统计数据不够准确,那么您认为通过这个模型得出的预测结果的准确度会怎样呢?
雷鼎鸣教授:中国的统计数据的确有些缺点,我们非常明白这一点。不过中国的统计数据也在慢慢改进。我们用的这个模型算是世界上比较尖端的方法,但是方法尖端,假如数据不准,得到的结果还是会出问题的。我觉得这其中还有两大问题。
第一,我们用的是每一个季度的数据来做预测,但是中国的统计数据(季度的数据)不是很长。最早的大概在90年左右,到现在也只有十多年,每一年有四个季度,加起来有几十个observations。不过我们主要不是看有多少个observations,而是看这些数据经历了多少个商业周期。经历过的商业周期越多,数据里面包含的信息就会越多。十多年是不够的,如果有二十年以上,经历了两三个商业周期,结果就会好很多。我们用同样的方法,用香港的数据来预测,是很准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的数据比较长。
第二,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GDP的数据。政府宣布出来的数据不一定是真实的数据,很多时候是政府目标的数据。我们发现,假如我们把过去十多年以来增长目标的数据都放进这个模型里面,目标的预测能力是很强的,预测的结果和宣布的数据相差很小。这样我们难免会怀疑宣布出来的数据是否真实。再举个例子,某一年某一个季度GDP的某个组成部分的数据可能可以在这个季度使用,也可以推到下个季度。究竟是这个季度用还是下个季度用,这中间的问题不好处理。其实这个问题在世界上很多政府的统计数据中都会出现,可能出于某些政治的考虑。是否真的如此,我们也很难判断,我们只知道预测的目标和最后的结果如此接近有些可疑。从这个角度看,就算宣布出来的数据跟我们预测的不一定完全一样,也不能判断我们是对是错。
另外,我们做预测光有数据是不够的,一定要明白中国经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跟李稻葵教授,跟社会科学院的一些朋友都认为应该看社会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我们所预测的结果。
记者:雷教授,您曾经说过“自由竞争的概念,一千年都不会过时”。现在,中国已经把反垄断法提上了人大常委会的议事日程,您认为中国这么迫切地提出反垄断法,有没有必要?
雷鼎鸣教授: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因为经济学家一般都是非常支持自由竞争的,一有垄断,所谓的“deadweight loss”就会出现。但是小部分项目,比如创新,需要给它垄断权来激励创新。有些产业也有规模效应,所以也要给它们一些垄断的空间。另外,我们要判断出垄断的严重程度,不是看企业的数量,严格来说,是要看价格和边际成本的差别有多大。但边际成本很多时候是得不到数据的,也很难准确地测算出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完全竞争的,价格和边际成本总是会有差别的。假如这个差别比较小,我们应该不去管它;假如差别比较大,我们就要看看市场结构是不是出了问题,是不是很多企业根本不能进入。反垄断法的出发点一般都是很好的,目的都是为了降低垄断所造成的福利损失。但是很多情况下,反垄断法起到的效果可能是负面的。这主要要看法的细节是怎样的,具体执行的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
我用我最熟悉的例子来说吧:香港现在也在讨论要搞一个《竞争法》,目的也是反垄断,具体的细节还没有提出来。大概在1996年的时候,香港曾经有一个消费者委员会,他们做了研究,提出了一些法律建议。我当时看到这些,觉得很危险,这对经济破坏可能是很大的。他们有好多建议,由于时间关系,我只举几个例子,其中一个是“捆绑销售是违法的”。但是我们看到市场中很多捆绑销售也是很有道理的。比如,我买一双鞋子,为什么要买一双?我买一套西装,为什么一定要成套买?这些本来在市场中都已经被接受了,但是一旦立了法以后,这些都成了违法的了。当然,立法的原因不是要禁止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有了法律概念以后,法律就要遵守。我再举一个例子:上游定价。比如,你买一本书,书后印有价格,出版商定了价,然后书店根据这个价格来出售,这个已经是犯法的了。因为他们(消费者委员会)说出版商垄断,统一了书店的价格,而不同的书店应该允许不用的价格,允许竞争。本来这些都是很合理的,降低了咨询的成本。但是一有了这个法以后,就干扰了市场。还有所谓进口货品的经销商不能只有一个,为了防止垄断。但是假如很多商家去经销,那么这些批发商中就没有人愿意去宣传广告,这里面存在一个free rider的问题。
反垄断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写这个法律的人不是经济学家,一般的法律专家对经济的了解并不多。美国是全世界中法律受到经济学影响最大的国家,美国的法庭中引用得最多的是经济学的论文,但是还是出现了不少违反经济学的问题。所以反垄断法的订立是一个需要非常谨慎处理的问题。
记者:您在2006年10月6日的《信报》上发表了《最低工资缺乏学理依据》一文,您检索了最近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界有关最低工资问题的文献,发现最新的专业研究结果又是压倒性地支持最低工资不利弱势社群就业的说法。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经济学家们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大多否定最低工资制,而另一方面,几十个国家的政治领袖们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采纳最低工资制。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雷鼎鸣教授:这个不算奇怪。经济学虽然是所有社会科学中对政策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学科,但是立法最终都是利益集团相互较劲的结果。关于压倒性的“最低工资对经济不利”的说法,我还想多说几句。NBER上有Neumark和Wascher的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写得非常平衡,对过去20多年的文献作了一个综合的评价。他的结论与我的一致,压倒性地认为最低工资对就业有负面的影响。本来劳动经济学中对于最低工资的讨论是没有什么人感兴趣的,经济学的结论都认为最低工资一定是不利于就业的。主要是90年代初期有几篇文章,如David Card 和Alan Krueger 以及Lawrence Katz写的几篇文章,说最低工资对就业有好处。因为这几位经济学家都是很有地位的,而且方法看上去很合理,所以很少有人置疑。在1996年1月美国经济学年会上,有一个研讨小组对他们的结论进行了批判,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性很大。95年以后的劳动经济学研究还发现他们的研究方法存在问题。他们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研究New Jersey和Pennsylvania这两个州的最低工资问题,采用的是电话问卷的调查方式;后来其他人用真实的数据得出相反的结论,这也证明了最初的问卷设计存在问题。
最近有一种新的说法,假如最低工资上涨10%,就业人数只是减少5%,那么对劳动者还是好的。但是这个说法存在不妥之处。第一,仍存在5%的失业,而且是境况更糟、更需要帮助的5%;第二,西方国家有些劳动需求弹性比较低,增加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不是很大。所以我们要弄清楚他们研究的背景,这些研究对于中国是不是适用的。另外,提高最低工资可能导致企业的地理位置的转移。比如说,如果在香港提高最低工资,很多企业就会转移到大陆,出现劳动力替代现象。中国有6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不断有人从农村进入城镇,在城市中采用最低工资,其效果很复杂。因为农村生产力比较低,企业不会转移到农村,但最低工资对于农民进城是很不利的。农民的生产力比较低,如果设定最低工资就不会有人愿意雇用他们,城市里的失业减少了,也限制了农村人民的竞争。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推出最低工资的政策时,是为了导致南部生产成本提高,根本就是政治小集团之间的斗争,而不是出于道德的原因。从“最低工资”得利的只是社会中生产力刚刚超过最低工资的一部分人,因为最低工资消除了潜在的竞争。中国的情况稍有不同,要看最低工资的水平,并且各省市地区也不尽相同。
在我看来,最低工资并不能解决收入不平衡问题,最低工资还会把这个问题弄得更严重。要解决这个问题,可用Milton•Friedman从前提过的negative income tax方法。意思是说,如果工作的工资太低,可由政府给予补贴。这也不是最好的方法,但是比最低工资好。最低工资打击了最需要帮助的人,最需要积累工作经验的人反而得不到就业机会。
记者:雷教授,您在香港的大学里任教,又常来大陆讲学,您觉得在经济学领域中,大陆的研究生教育与香港的研究生教育主要有哪些区别呢?希望您能给我们大陆的学生提一些学习的建议。
雷鼎鸣教授: 坦白地说,香港和大陆的经济学教育都还没有足够高的水平。香港的情况和大陆不太一样。香港是没有足够规模的研究院,愿意留在香港的博士不是很多。香港的硕士分两种:MSc和Mphil。MSc是以选课方式来完成学位教育的;Mphil是以做研究的方式。我们的MSc硕士中90%是大陆的学生,并且数量也基本没有问题。但研究就是规模不够,人数不够,成本太高。这些学生中,最优秀的往往会申请到国外的大学继续学习。在课程设置方面,香港基本上是和国际接轨的。在大陆,课程不一定与国际接轨,且必须读完硕士才能读博,而美国是没有硕士学位的。我1999年在CCER教书,当时感觉国外的教材并不多,不过现在已经引进了很多原版教材,但还有继续改进的余地。关于论文水平,我觉得大陆的论文水平参差不齐,论文水平与导师的关系也很大。即使是大陆最好的大学中,也有论文水平达不到相应的国际标准。很多论文的选题存在问题,技术水平差别也很大。年轻人往往太关注工具的作用了,但技术再好也不能取代经济思想的。这样,写出来的论文只是一个作业,而称不上是一个贡献。
中国的创新方面不够,我看这个问题不仅出在研究院,其实在本科就出现了。中国的本科教育太狭隘了。我本科是在Chicago大学读的,在45门课程中,仅要求8门与经济学相关。现在是42门课,经济学仍只占8门。而相比之下,大陆的经济学课程太多了。这样导致的后果是:经济学研究院中,几乎所有人的背景知识都一样,思想方法也大同小异。这种状况对研究很不利。所以我们在香港推动本科教育的改革,提倡本科期间多搞一些通识教育。国外常常要求学生读一些Classics的东西,训练学生的批判精神,而这种批判精神有利于学生日后的创新。中国本科生中的经济学课程分得太细,其实把握好基础,很多知识是融会贯通的。当然中国的研究生也有优点,基础扎实,技术水平很高,有些技术水平特别高的人,即使没受过广泛的通识教育,在研究方面还是会做出很大的贡献。中国在国外读博士学位的留学生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但真正能在国际被公认为一流学者的屈指可数。这一点,香港比大陆要好,香港的学生比大陆的思维要开阔一些。所以我觉得改革要从本科生开始,要培养创造性,请大师来讲座等等。
[[image1]]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2022年预聘教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是以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毕业的马寅初学长命名的一所与国际接轨、高起点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招聘事业编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招聘事业编制研究员2名。北大汇丰智库研究实习岗位招聘启事
北大汇丰智库将于2020年起招聘实习研究专员若干名。
-
斯蒂芬·罗奇:日本货币政策迷思
51人看过
-
林毅夫谈全球增长与中国发展
53人看过
-
中国房地产这些数字让外国人震惊!
91人看过
-
马凯硕:西方资本主义的三宗罪
64人看过
-
农行董事长蒋超良空降吉林 曾助王岐山应对金融危机
74人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