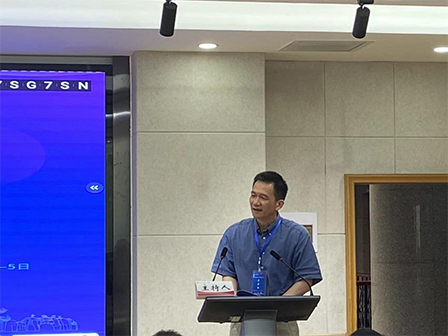北京行
观点 · 1999-10-28 00:00
返回因为进入了半退休状态,多点时间做校外的事,今年开始我就答应了好些大学去讲话——国内所说的作报告。前些时去了武汉的华中理工学院及武汉大学作过两次讲话,一个座谈。这两次讲话的录音被整理后发表在《经济学消息报》...
因为进入了半退休状态,多点时间做校外的事,今年开始我就答应了好些大学去讲话——国内所说的作报告。前些时去了武汉的华中理工学院及武汉大学作过两次讲话,一个座谈。这两次讲话的录音被整理后发表在《经济学消息报》上,获得颇大的反响。后来我找到这两份发表的原文,很满意,也使我意识到今天大陆的学子,其理解能力明显地在我们港大的学子之上。
到北京作讲话,只有四天时间。我见婉却了那么多年,就可接尽接,结果在四天之内作了三次座谈,五次演讲。我作演讲是从来不用作准备的,但讲前要很松弛,脑中要一片空白,才可以讲得好象是准备了的。所以在北京每天我早睡早起。话虽如此,四天之内讲八次话——其中一天讲三次——自己从来没有试过。全力以赴,讲来不过不失也算是不错了。
北京的讲话,比不上武汉的。主要原因可能不是过于频密,而是北京交通挤塞,动不动就是一个小时不安宁的车程,使我的脑子不能静下来。
十月十日晚抵北京,十一日早上起来先要做两件事。第一是要到永玉的万荷堂欣赏一下;第二是要赶到故宫去参观五十周年所展出的中国古书画精品。
永玉自己精心制作的万荷堂,有口皆碑,他曾经邀请我到那里小住好几次了。果然名不虚传。是很大的地方,大概有六、七座仿古的建筑物——凡建筑、家具、陈列,就是植物的品种皆古。我虽然对中国古代的文化有点研究,但比起永玉就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怎样说,我就怎样听。可惜只能在那里勾留了两个小时。总有一天我会去小住,细心地研究一下。
赶到故宫,竟然找来找去也找不到精品展出的地方!真的莫名其妙。这样重要的展出,却没有告示指引,而问了几个工作人员,竟然没有一个知道。秋高气爽,我们三个人在故宫内东奔西跑,身水身汗,终于还是找到了。果然是精品,王珣的《伯远帖》,李白的《上阳台》,历历在目,而展场中只有三几个人,使我觉得是进入了一个奇异的世界。
在展览场内只能欣赏半个小时,就要赶到新华基金作座谈。谈的当然是关于近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座的都是该基金的年青职员,知识水平很高,但他们跟后来我遇到的其它青年一样,答错了我提出的一个问题。
我问:假如今天中国废除外汇及有关的管制,人民币会升值还是贬值呢?他们都答会贬值。答错了。但当我继续问:假如今天香港政府宣布下个月会实施外汇管制,香港的外资会增加还是会跑掉?他们都说会跑掉。答对了。我再问:那么为什么你们说废除汇管人民币会贬值呢?他们无言以对。
十二日正式“开波”,上午先到人民大学进午餐,跟着的讲题是《不要把中国人小看了》。不是学术性的,内容是说中国人不仅刻苦耐劳,工资低廉,而近几年来中国的青年学得很快,连知识及天分的价格也相宜之极,参加国际上的生产贸易竞争,是不需要任何政府的保护的。事实上,保护缚手缚脚,与老外竞争起来诸多不便,凶多吉少也。虽然那些所谓“保护”是维护特权利益,但无可避免的印象是小看了自己中国人。
下午五时转到北京大学,晚餐后的讲题是《高斯定律的谬误》。这个及后来的三个讲题都是学术性的,是自己数十年来从学术生涯中所得的一点收获,天天想,想了数十年,当然是驾轻就熟了。
十三日早上先到天则研究所座谈。这是个很有分量的研究所。他们要搞一个“中华新制度经济学会”,出一些刊物,请我作名誉会长。我对名誉没有兴趣,推却了,但我很欣赏他们的意图,所以答应了会尽可能多给他们的刊物写文章。
是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六十年代我和高斯等几个人搞出来的、今天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大门学问在中国很风行,而天则的人材有的是,这学会是会办得很好的。
中午到北京师大进午餐,跟的讲题是《快要失传的价格理论》,内容我曾在《壹周刊》发表过。晚上到清华大学,晚餐后的讲题是《经济解释》,那是涉及科学的方法了。
最后一天,十四日,早上与几位国务院的朋友座谈,说的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到机场的途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午餐,跟的讲题是《交易费用与经济效益》,是自己发明的一些观点。
这次北京之行,有四点要写下来的。第一,最重要的,是北京的学生真的很了不起。我想,要是四十年前这些学生有我的际遇,在美国得到大师指导,我怎样也比他们不过。第二,五间大学请我吃的午餐或晚餐,其食品水平远超香港的所有大学。其三,首两次演说我用英语,到了第三次,翻译的青年学者翻了十多分钟后,突然说:“我要请张教授用普通话讲,他讲得不对我从旁协助。”我没有他的办法,于是逼试用普通话。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以普通话演说,余下来的其他两个演说都是用普通话,虽然说得一塌糊涂,但对我来说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了。
最后一点是在五间名校的讲话,座无虚设,而站的人多的是。这种破纪录的英雄式的接待,主要是因为我十五年前出版的《卖橘者言》。据说这本旧作在国内曾经有手抄本。八八年在四川再版时被抽起了一些比较敏感的文章,三万二千本一下子卖光,影印本广泛流传。
香港的学者,是要多用中文写些有教育性的文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