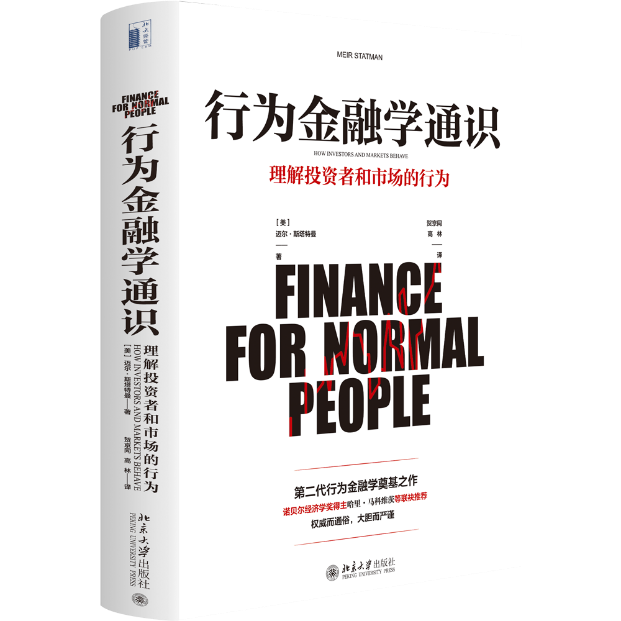宁向东:从容与淡定
书刊 · 2009-06-23
返回只有内心里根本不把虚名当回事,才能够行为洒脱,泰然自若。
从容与淡定,是我最羡慕的两种品质,羡慕是因为做不到,求之不得。最早感悟到这两种气质是看白岩松对日本作家渡边淳一的访问。那位以写中年人的爱情入木三分而闻名于世的老人,在谈论关于人生理解的时候,无论神态还是言语方面都从骨头缝里渗透出这些高贵的气质。我想,这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拥有的气质,也不是随便什么时代和什么环境里都能孕育出来的气质。
近日重读《上学记》,突然意识到何兆武先生也是具备这些气质的人。而且,何先生是极少数真正拥有这些气质的中国人之一。在当下的中国,人们愿意用一些好听的词汇、充满光环的帽子来奉承人。奉承别人的人别有用心,被奉承的人也常常欣然受之。比如,很多架着昂贵眼镜的商人愿意被人称为“儒商”,但做起事来该儒的时候商,该商的时候却乳臭未干。只不过做秀的本事大一些,其实与儒商的内涵毫不相干。所以,在我看来,当今中国什么东西都可能是假的,包括品质。
我与何兆武先生不熟,只是他众多的学生之一。后来,虽在一个楼中上班,但差着辈分,学科也不同,常常只是用目光表达敬意,极少攀谈。何先生是清华的宝贝,但似乎清华并不太懂得如何珍惜。至少是在十几年前,何先生“年富力强”的时候。清华的文科领导叶公好龙,因为是外行,所以不识货,常常重视挖来的一些假货,对家中的宝贝却并不留意。如果他们懂得把已经在册的教师充分发挥作用,不知会比他们满世界地“寻花问柳”效果要好多少。
我做何先生的学生,是在1986学年。何先生当时在为社会科学系的研究生们讲“西方思想史”。我当时虽然专业是经济管理,但对人文知识和社会科学的兴趣盎然,也跑去旁听。记得那间小教室里常常人满为患,晚到之人需要从其他教室搬椅子。不仅仅是研究生,很多年轻教师也来旁听。李润海教授门下有几位年轻女教师,个个貌美如花,是那些男研究生们课间的谈资。我那时还少不更事,更多的兴趣还是何先生的课,特别被他上课时的魅力所吸引。
何先生的博学是我最佩服的。他常常英文、希腊文、德文并用,来解释一段思想的历程。他有时也会从口袋中取出一些小纸条,上面是他用自称不懂的文字(我们就更不懂了)所记录的概念,他必须借助于那些纸条才能将之抄录在黑板上。
何先生的课固然讲得好,但我多数都没听懂。虽然当时情绪盎然,也借了一些何先生推荐的、课上提到的甚至他自己翻译的书来看,比如《历史的观念》,但真正的精华,我吸收得并不多。现在想来,收获倒有两个:一是借这个机会读了一些我看得懂的世界名著,如房龙的《宽容》之类,恶补了自己在世界文明知识方面的不足;二是培养了一点人文的意趣,也领略了大学问家的教书风采。
我与何先生私下的接触只有一次,而且当时备受打击。记得我在读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书中有一些问题我搞不懂,就与朋友们讨论。程钢兄当时正在做研究生,跟何先生钻研西方哲学史,他自告奋勇带我去请教何先生。何先生听我讲完来意,非常客气地对我说,经济学的问题我不懂,你问我这些问题找错了人,随即便将话题转到了其他方面,并如算命先生一般看了我一阵,然后说:“你是旗人吧。”他这个本事神乎其技,至今我也没有搞清楚他是怎样推断的。
何先生直白地对我说“我不懂”,给我的热情泼了冷水。我当时感觉他拒人千里。他的举动也是我先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我平时所遇到的老师,通常是有问必答。在我的心目中,老师向来都是百科全书。但后来,随着我的成长,我知道了何先生的与众不同,也让我懂了什么是学者的严谨,什么叫不知深浅。一个学者,能够对一个认真的学生说“我不懂”,而不是泛泛地即兴地谈些感觉,发些议论,这是对于知识何等的敬畏,对自己何其严格的要求!正是由于何先生给我的先例,后来我也试着对学生说:“这个问题我不懂。”渐渐地,我发现恰到好处地对学生说出“我不懂”,其实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自信。
在上世纪90年代,我住在清华校园内,时常还能见到何先生,他戴着那种老式的网球帽、标致性的,穿着灯芯绒长裤,骑着自行车的样子,常常在我的目光的追随中慢慢远行,是我记忆中不可磨灭的部分。2006年秋天,就在《上学记》出版的时候,我在杂志上读到何先生的专访,并看到一张照片,感觉他稍显老态,但依然笑容可掬,非常闲适。这两天,重读《上学记》,我突然意识到,何先生的气质其实就是我所要追寻的“从容”与“淡定”。
我猜想,正是他自己心中没把大师的虚名当回事,所以才会行为洒脱,泰然自若。最能体现何先生从容淡定的一件事莫过于葛兆光先生在书序中所提到的:当前几年清华为何先生办一个祝寿会的时候,学问大家云集,鸿论蓄势待发,却找不见何先生本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