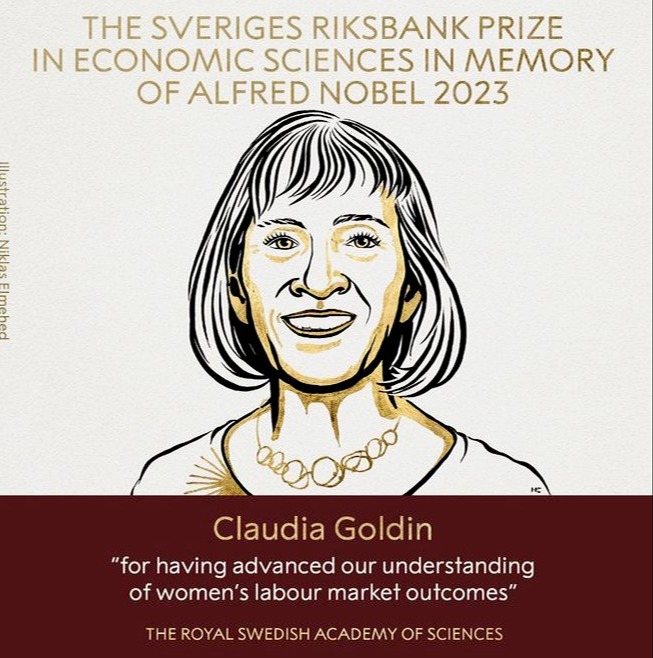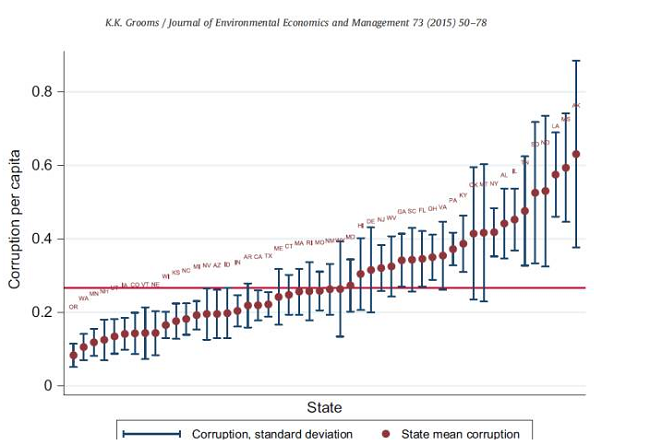为什么治理经济“过热”重在治理银行?
观点 · 2004-09-16
返回讲演:
为什么治理经济“过热”重在治理银行?
--张军教授最近在上海财经大学学术节的演讲(节选)
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学界就一直在讨论着中国宏观经济是否过热以是全面过热还是局部过热的问题。到今年年初,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结论,那就是中国经济已经积累了由局部的投资过热引起的经济过热的压力。在今年第一季度的宏观数据公布出来之后,投资需求的过热得到了印证。紧接着,来自国务院以及下属发改委、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土资源部等集中在4月中下旬出台了一系列包括货币政策、金融监管以及“道义劝说”在内的调控措施试图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贷款规模的过快增长。中国经济能否成功地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再次成为当下全球关注的焦点之一。
今天,在我的演讲里我将首先说明,我们是如何来判断经济的过热现象的?为什么在经历了10年的轻度的通货紧缩之后我们的经济又再度出现投资过热?如何来解读这一轮的宏观调控政策?最后,中国经济以怎样的方式着陆?能避免出现大起大落吗?
为什么说宏观经济出现了“过热”的趋势?
我们对宏观经济形势的理解和判断往往基于理论的逻辑和以往的经验指标,而且这两者相互作用。比如,要判断经济在总量上是否已经偏离了“均衡”的轨道,在理论上我们必须拿经济的实际总量与均衡时的总量水平去比较。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知道我们的均衡水平可能在什么位置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经验值,它可以简单地通过以往经济增长率的“均值”来获得,也可以从以往长时间的数据中“拟合”出来,比如“菲利普斯曲线”或“奥肯定律”就是用统计拟合出来的反映宏观经济的重要变量之间的经验关系。
从经验上看,中国在1978-1994年间经济增长经历了三次大起大落的波动,每次“大起”均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速引起,投资在短期拉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并伴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发生。这15年的经历提供了这样几个经验关系:第一,在短期,投资增长过快是经济增长提速的主要原因;第二,经济增长提速势必引起通货膨胀的发生;第三,当经济增长率显著高于8-9%(这相当与15年来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的时候,通货膨胀的压力必然增大。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经验就成为了我们判断宏观经济是否出现不均衡或不稳定态势的主要“参照值”(reference point)。
其实,从去年“非典”被控制住之后,尤其是到了去年的下半年,经济学界就有了对经济增长出现加速的关注。去年的第4季度,GDP的增长出现了几乎两位数的高位,全年达到了9.3%,紧接着在今年第一季度达到9.7%的高位,达到或者超出了我们的“参照值”,这就提醒了经济学家和政府,在经历了10年的宏观稳定之后,我们的经济可能开始重新恢复了高增长的“能量”。从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中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个过热的征兆。连续数月出现40%以上乃至50%的投资增长率,显然已经达到了1994年之前的记录。基于以往的经验值,说我们的经济当前已经有了投资“过热”的征兆,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今年第一季度,我们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3%,在一些行业,比如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等,投资同比增长了1倍多。这是10年来我们未曾见过的经济高涨局面。
我想,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非典”的流行,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肯定还更早一些。至于说经济是局部过热还是全局过热,其实是无谓的,因为投资增长的加速总是从局部开始的。比如,汽车投资需求增加过快总是会使对钢材的需求(包括进口需求)增加过快,短期内使钢材的价格上涨,而后者会吸引更多的投资投向钢铁部门,从而引起钢铁部门的投资需求增加过快,依次类推。应该说,经济过热总是由局部的投资过热引发的,但没有什么局部的过热经济。
一旦局部的投资过热引发的投资连锁过热遇到基础性的或资源性的“瓶颈”部门时,这个投资的连锁效应就中止了,取而代之的是物价水平的连锁推动。比如,钢的投资需求过快必然在短期增大对煤炭和铁矿石的需求,一旦煤炭和铁矿石的供给因为资源约束而无法满足时,它们的价格就可能上升或者在价格被认为管制的时候出现严重的短缺。这种情况就是教科书里谈到的“需求拉起”的通货膨胀的生成逻辑。当然了,我们迄今还没有真正出现通货膨胀,消费价格指数(CPI)在今年第一季度同比上涨了2.4%。说明现在还没有发展到出现严重的基础性和资源性“瓶颈”的地步,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压力还在不断形成之中。应该说,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共识。
但是,这并不是说大家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看法就完全一致了。其实不然,经济学家在一些问题上还是有不少分歧的意见,有的看法与政府的基本主张也不完全一致。经济问题就是这样复杂,不能指望经济学家在许多问题上只有一种声音。其实,我们每一次经济的“大起”,都引起经济学家的争论与广泛的讨论。我清楚地记得90年代那一次经济学界对经济过热的热烈讨论。对政府来说,经济学家之间的热烈讨论比只有一种声音对政府的决策过程更重要。
为什么投资增长最终加快了?
回顾中国25年来所经历的三次大的宏观经济波动,每一次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毫无疑问都是由投资过热引发的。固定资产的投资需求高涨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10年前的那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开发区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的浪潮引发。这一次除了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之外,还有汽车等新兴部门的高度繁荣引起。可以这么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投资需求的增长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真正令我们今天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10年前的那次经济“大起”之后没有像80年代两次发生的那样很快又进入新一轮的“大起”,而是拖了很长的“尾巴”发生了10年之久的“通货紧缩”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来更好地理解本次的经济过热以及对治理经济过热的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出更好的评价。
不管这次的投资过热的导火线在哪里以及主要由什么部门的投资需求的扩张引发,实际发生的是银行的信贷扩张的的确确加快了,自去年夏天以来,商业银行的贷款平均以20%以上的速度在增加,高的时候达到24%。今天我们对“信贷”二字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今天在我们这个经济里面企业为投资项目融资的似乎就只有银行,直接融资(企业债的发行更是微不足道)相对于间接的或中介融资的比例非常小。这显然和国家融资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生的变化及金融发展的结构有直接的关系。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实行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所谓“拨改贷)之后,中国的金融系统就很快演变成了由银行所主导的体系。在这个融资体系下,中国的企业面临着的是一个高负债的资本结构。这还不要紧,要紧的是,由于我们的大多数企业缺乏赢利能力,所以这种高负债的资本结构必然增大了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对于一个由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来讲,投资的收益风险必然传递给银行,变成银行的债务风险。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非常重要。
对中国的金融体系的特征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知识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回答上面的问题了。回想一下,我们为什么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经济频繁的“大起大落”而在90年代中期以后却进入了长达10年的轻度的“通货紧缩”时期?其原因主要不是因为投资缺乏需求,而是由于银行信贷的供给收缩导致的。在“拨改贷”之前,企业的负债率和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均较低,政府对投资过热的实施紧缩的政策不太会改变银行的风险状况,所以日后的经济会很快得到启动、复苏和高涨;但“拨改贷”后,企业的负债率平均高达90%,银行的风险组合被彻底改变了。尤其是当90年代初的那场投资过热被严厉的“紧缩”政策解压下来之后,大量的贷款收不回来变成了坏帐,银行的坏帐和风险必然一下子大幅度增加了,引发了“隐性的”债务危机,结果导致中国的银行系统的呆坏帐比重在此之后急剧性地上升,即使按官方公开的数据也平均高达25%以上,这必然严重制约了商业银行系统的信贷创造的能力,使中国的金融体系始不得不终处于风险控制的谨慎运作模式之中。事实上,10年来,中国的金融当局和商业银行不得不一直采取过度谨慎的方式(所谓“零风险”经营)和“惜贷”来消化银行坏帐,这导致后来的企业投资需求受到抑制,经济的增长不得不转向主要依赖政府的“公共投资”(国债或财政政策)来支撑的局面。从统计上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开始急速恶化,赤字持续增长。
一个银行主导的融资体系下,经济过热的出现都最终是银行的信贷扩张的结果。这一次的经济过热也不例外。但我们要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商业银行“惜贷”了这么久的时间之后今天敢于这么“放贷”了呢?我想,从银行方面来讲,第一,在经历了长达10年的通货紧缩和“惜贷”之后,银行在消化呆坏帐、充实资本金和改善风险管理方面有了显著的“长进”,现在的不良贷款率已经从25%以上下降到了18-19%的水平,银行的信贷创造的能力大大改善;第二,这两年开始的商业银行降低呆帐率的“运动”在实际上提高了银行信贷扩张的动机(所谓扩大信贷分母的运动);第三,这些年来,中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数量催生较快,除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我们现在有11家股份制银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3家政策银行和4万多家信用社等。
再从经济基本面来讲,由于市场主导的作用加强,信贷的增长和流向多以投资项目的赢利能力为基础,这可以从投资“更热”的领域来判断。钢铁、水泥、电解铝等在市场上都是需求过旺和价格增长较快的产品,信贷上支持这些部门自然是符合“商业实践”的行为。另外,我想指出的是,根据调查和统计发现,这次的投资需求增长加速与投资主体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几乎可以断定的是,民营企业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投资规模最大的地方。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浙江、江苏和广东最为典型。主导地方投资增长的是民营企业和混合的民间资本。这些投资更多地是基于市场的赢利机会,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它们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更不能简单地断言它们的投资因为不完全符合国家的产业指导政策而不合理。问题在于,我们的经济中还有一大块没有效率的投资需求,它们表现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开发区建设以及对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等,我们体制中的这些顽症并没有被制止下来,而且由于预期的作用,甚至可能出现了突击投资和大胆跟进的现象。因此,真正要下决心挤压下来的投资需求应该主要是那些没有效率的政府投资,而不能叫停那些迎合市场和赢利前景好的投资需求。
为什么治理过热投资重在治理银行?
如上所述,最近这几年,商业银行方面贷款能力的显著改善和地方上总是存在的旺盛的投资需求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共同引发了这次的投资膨胀,产生宏观上的经济过热的压力。如何化解这些压力,解决好过热压力的形成因素,主要取决于我们对当前出现的投资增长过快的趋势是否可以抑制住。这就涉及到宏观治理政策的选择问题。政策上最大的挑战是不容易找到最适时、最适合和最适度的政策。这好比用药,既要剂量得当又要用副作用最小的药。这非常不容易,需要多方面的智慧和经验。一般来说,在控制总量的膨胀问题上,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往往是最重要的手段。在美国或发达的市场经济里,“升息”往往是“金牌”手段。因为升息提高了融资的(机会)成本,有助于抑制投资需求和对信贷需求的过快扩张,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一旦解压了,货币当局可以再逐步降息或(和)采用财政和收入政策来恢复经济的增长。所以,在治理宏观经济波动问题上,通常央行(货币当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我们的经济,要化解掉这些通涨的因素,在短期似乎也只能想办法将投资需求过快的增长减慢下来,在这一点上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的问题与西方有所不同的是,第一,中国的政府体制不同于西方,我们可动用的调控政策除了货币政策之外,我们也有行政手段可以用于控制投资过热;第二,中国的投资需求几乎全然是依靠银行的信贷来支持的。这使得我们的宏观治理更加复杂了。例如,旨在抑制投资需求过快增长的紧缩性政策要么不怎么起作用(如提高利率),要么会在短时间里迅速增加银行的坏帐规模(如对在建投资项目的行政“叫停”)。但是,如果经济过热得不到及时的治理,以至于最终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不得不全面叫停时,银行的坏帐会更严重,规模也会更大。从上一次的经验教训来看,在不得不实行严厉的叫停政策之后,银行的坏帐大幅度地增加了,这在日后就为银行普遍出现的“惜贷”和过度谨慎的信贷行为提供了理由。其结果,紧缩政策之后可能就无法很快、很好地启动经济的投资需求,因为银行系统要花很长的时间来消化不良信贷,导致长时间的宏观“紧缩”。
因此,现在对中国的投资膨胀和经济过热的治理就应该充分考虑到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是要控制过快增长的贷款规模,因为贷款规模增长过快会导致银行潜在的风险急剧增加。但问题是,这些激增的贷款大部分是流入了房地产、钢材、水泥、电解铝等行业,因为这些行业的市场行情和预期盈利都不错,而一旦实行严厉的行政性紧缩和叫停后,这些行业的价格如果出现大幅回落,会导致这些目前尚好的项目变坏,使本来隐性的、或有的贷款风险变成真的呆账坏账,在短期急剧加大银行的风险。因此,简单的行政性叫停是要慎用的。
既然这样,在治理中国当前正在形成的经济过热时,我们就不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主要依靠央行的货币政策将治理的重点针对投资“需求方”去考虑宏观的紧缩政策,我们更需要“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进行严格的监管与风险控制的措施。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同时对商业银行进行信贷和信贷风险的监管,仅仅靠央行提高利率往往并不能很好地抑制地方的投资需求的增长。所以,央行提高准备金率往往就比提高贷款利率更重要,因为提高准备金率将治理的对象针对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的增长速度。在中国,可以不把提高利率的政策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去考虑,重要的是,既要将商业银行贷款的增长速度降下来,又要不至于大幅度增加银行的呆坏帐规模。
而要做到这一点,“银监会”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银监会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需要特别策略性地将治理的重点放在新增贷款方面,而同时指令商业银行对已经发放的贷款加强风险的监管。从现有出台的政策来看,对于已经开工或者正在建设的项目所发放的贷款,银监会的确加强了对商业银行在审查和批准贷款申请中的“窗口指导”的作用,银监会应该要求银行加强和加大对已发放信贷的跟踪和风险监管,防止因贷款申请审查不严而可能导致的不良贷款形成的风险。银监会于4月13日已经发出的“通知”也是旨在对已经发放的贷款进行清理和监督的一种努力。实际上,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本来是商业银行的惯例,但在中国,这样的信贷监管往往流于形式,得不到真正的贯彻落实。所以,在投资出现过热的情况下,这样的信贷风险管理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我想,我们要力争实现经济“软着陆”,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就需要避免从经济过热转变成通货紧缩。而现在的投资过热并不必然导致未来的生产能力过剩和更严重的通货紧缩。其实,通货紧缩的发生不取决于现在投资是否过热了,而是取决于治理过热的政策是否过了头,是否严重伤害了经济的复苏能力。在中国,只要治理的政策不严重改变银行的风险组合和偏好,银行就能够在日后继续为总需求的复速和增长提供支持而不是采取过度谨慎的“惜贷”行为。只要容易重新启动需求,尤其是对生产能力存量的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本来是可以由市场自身(如破产、兼并和重组)来消化的。因此,当前的投资过热会不会带来更加严重的通货紧缩,关键的问题是,现在的治理政策要避免我们上面谈到的不要在短期过于加大银行方面的呆坏帐和风险。尤其是,当前的通货膨胀还非常温和的时候,加强对商业银行的信贷监管和风险管理,我们完全可能用比较温和的办法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不仅如此,从加强对银行的信贷监管和风险管理方面入手来治理投资过热,还将从长远改善中国经济的健康状况。
讲演:
为什么治理经济“过热”重在治理银行?
--张军教授最近在上海财经大学学术节的演讲(节选)
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学界就一直在讨论着中国宏观经济是否过热以是全面过热还是局部过热的问题。到今年年初,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结论,那就是中国经济已经积累了由局部的投资过热引起的经济过热的压力。在今年第一季度的宏观数据公布出来之后,投资需求的过热得到了印证。紧接着,来自国务院以及下属发改委、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土资源部等集中在4月中下旬出台了一系列包括货币政策、金融监管以及“道义劝说”在内的调控措施试图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贷款规模的过快增长。中国经济能否成功地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再次成为当下全球关注的焦点之一。
今天,在我的演讲里我将首先说明,我们是如何来判断经济的过热现象的?为什么在经历了10年的轻度的通货紧缩之后我们的经济又再度出现投资过热?如何来解读这一轮的宏观调控政策?最后,中国经济以怎样的方式着陆?能避免出现大起大落吗?
为什么说宏观经济出现了“过热”的趋势?
我们对宏观经济形势的理解和判断往往基于理论的逻辑和以往的经验指标,而且这两者相互作用。比如,要判断经济在总量上是否已经偏离了“均衡”的轨道,在理论上我们必须拿经济的实际总量与均衡时的总量水平去比较。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知道我们的均衡水平可能在什么位置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经验值,它可以简单地通过以往经济增长率的“均值”来获得,也可以从以往长时间的数据中“拟合”出来,比如“菲利普斯曲线”或“奥肯定律”就是用统计拟合出来的反映宏观经济的重要变量之间的经验关系。
从经验上看,中国在1978-1994年间经济增长经历了三次大起大落的波动,每次“大起”均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速引起,投资在短期拉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并伴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发生。这15年的经历提供了这样几个经验关系:第一,在短期,投资增长过快是经济增长提速的主要原因;第二,经济增长提速势必引起通货膨胀的发生;第三,当经济增长率显著高于8-9%(这相当与15年来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的时候,通货膨胀的压力必然增大。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经验就成为了我们判断宏观经济是否出现不均衡或不稳定态势的主要“参照值”(reference point)。
其实,从去年“非典”被控制住之后,尤其是到了去年的下半年,经济学界就有了对经济增长出现加速的关注。去年的第4季度,GDP的增长出现了几乎两位数的高位,全年达到了9.3%,紧接着在今年第一季度达到9.7%的高位,达到或者超出了我们的“参照值”,这就提醒了经济学家和政府,在经历了10年的宏观稳定之后,我们的经济可能开始重新恢复了高增长的“能量”。从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中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个过热的征兆。连续数月出现40%以上乃至50%的投资增长率,显然已经达到了1994年之前的记录。基于以往的经验值,说我们的经济当前已经有了投资“过热”的征兆,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今年第一季度,我们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3%,在一些行业,比如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等,投资同比增长了1倍多。这是10年来我们未曾见过的经济高涨局面。
我想,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非典”的流行,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肯定还更早一些。至于说经济是局部过热还是全局过热,其实是无谓的,因为投资增长的加速总是从局部开始的。比如,汽车投资需求增加过快总是会使对钢材的需求(包括进口需求)增加过快,短期内使钢材的价格上涨,而后者会吸引更多的投资投向钢铁部门,从而引起钢铁部门的投资需求增加过快,依次类推。应该说,经济过热总是由局部的投资过热引发的,但没有什么局部的过热经济。
一旦局部的投资过热引发的投资连锁过热遇到基础性的或资源性的“瓶颈”部门时,这个投资的连锁效应就中止了,取而代之的是物价水平的连锁推动。比如,钢的投资需求过快必然在短期增大对煤炭和铁矿石的需求,一旦煤炭和铁矿石的供给因为资源约束而无法满足时,它们的价格就可能上升或者在价格被认为管制的时候出现严重的短缺。这种情况就是教科书里谈到的“需求拉起”的通货膨胀的生成逻辑。当然了,我们迄今还没有真正出现通货膨胀,消费价格指数(CPI)在今年第一季度同比上涨了2.4%。说明现在还没有发展到出现严重的基础性和资源性“瓶颈”的地步,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压力还在不断形成之中。应该说,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共识。
但是,这并不是说大家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看法就完全一致了。其实不然,经济学家在一些问题上还是有不少分歧的意见,有的看法与政府的基本主张也不完全一致。经济问题就是这样复杂,不能指望经济学家在许多问题上只有一种声音。其实,我们每一次经济的“大起”,都引起经济学家的争论与广泛的讨论。我清楚地记得90年代那一次经济学界对经济过热的热烈讨论。对政府来说,经济学家之间的热烈讨论比只有一种声音对政府的决策过程更重要。
为什么投资增长最终加快了?
回顾中国25年来所经历的三次大的宏观经济波动,每一次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毫无疑问都是由投资过热引发的。固定资产的投资需求高涨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10年前的那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开发区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的浪潮引发。这一次除了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之外,还有汽车等新兴部门的高度繁荣引起。可以这么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投资需求的增长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真正令我们今天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10年前的那次经济“大起”之后没有像80年代两次发生的那样很快又进入新一轮的“大起”,而是拖了很长的“尾巴”发生了10年之久的“通货紧缩”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来更好地理解本次的经济过热以及对治理经济过热的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出更好的评价。
不管这次的投资过热的导火线在哪里以及主要由什么部门的投资需求的扩张引发,实际发生的是银行的信贷扩张的的确确加快了,自去年夏天以来,商业银行的贷款平均以20%以上的速度在增加,高的时候达到24%。今天我们对“信贷”二字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今天在我们这个经济里面企业为投资项目融资的似乎就只有银行,直接融资(企业债的发行更是微不足道)相对于间接的或中介融资的比例非常小。这显然和国家融资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生的变化及金融发展的结构有直接的关系。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实行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所谓“拨改贷)之后,中国的金融系统就很快演变成了由银行所主导的体系。在这个融资体系下,中国的企业面临着的是一个高负债的资本结构。这还不要紧,要紧的是,由于我们的大多数企业缺乏赢利能力,所以这种高负债的资本结构必然增大了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对于一个由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来讲,投资的收益风险必然传递给银行,变成银行的债务风险。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非常重要。
对中国的金融体系的特征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知识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回答上面的问题了。回想一下,我们为什么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经济频繁的“大起大落”而在90年代中期以后却进入了长达10年的轻度的“通货紧缩”时期?其原因主要不是因为投资缺乏需求,而是由于银行信贷的供给收缩导致的。在“拨改贷”之前,企业的负债率和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均较低,政府对投资过热的实施紧缩的政策不太会改变银行的风险状况,所以日后的经济会很快得到启动、复苏和高涨;但“拨改贷”后,企业的负债率平均高达90%,银行的风险组合被彻底改变了。尤其是当90年代初的那场投资过热被严厉的“紧缩”政策解压下来之后,大量的贷款收不回来变成了坏帐,银行的坏帐和风险必然一下子大幅度增加了,引发了“隐性的”债务危机,结果导致中国的银行系统的呆坏帐比重在此之后急剧性地上升,即使按官方公开的数据也平均高达25%以上,这必然严重制约了商业银行系统的信贷创造的能力,使中国的金融体系始不得不终处于风险控制的谨慎运作模式之中。事实上,10年来,中国的金融当局和商业银行不得不一直采取过度谨慎的方式(所谓“零风险”经营)和“惜贷”来消化银行坏帐,这导致后来的企业投资需求受到抑制,经济的增长不得不转向主要依赖政府的“公共投资”(国债或财政政策)来支撑的局面。从统计上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开始急速恶化,赤字持续增长。
一个银行主导的融资体系下,经济过热的出现都最终是银行的信贷扩张的结果。这一次的经济过热也不例外。但我们要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商业银行“惜贷”了这么久的时间之后今天敢于这么“放贷”了呢?我想,从银行方面来讲,第一,在经历了长达10年的通货紧缩和“惜贷”之后,银行在消化呆坏帐、充实资本金和改善风险管理方面有了显著的“长进”,现在的不良贷款率已经从25%以上下降到了18-19%的水平,银行的信贷创造的能力大大改善;第二,这两年开始的商业银行降低呆帐率的“运动”在实际上提高了银行信贷扩张的动机(所谓扩大信贷分母的运动);第三,这些年来,中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数量催生较快,除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我们现在有11家股份制银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3家政策银行和4万多家信用社等。
再从经济基本面来讲,由于市场主导的作用加强,信贷的增长和流向多以投资项目的赢利能力为基础,这可以从投资“更热”的领域来判断。钢铁、水泥、电解铝等在市场上都是需求过旺和价格增长较快的产品,信贷上支持这些部门自然是符合“商业实践”的行为。另外,我想指出的是,根据调查和统计发现,这次的投资需求增长加速与投资主体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几乎可以断定的是,民营企业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投资规模最大的地方。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浙江、江苏和广东最为典型。主导地方投资增长的是民营企业和混合的民间资本。这些投资更多地是基于市场的赢利机会,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它们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更不能简单地断言它们的投资因为不完全符合国家的产业指导政策而不合理。问题在于,我们的经济中还有一大块没有效率的投资需求,它们表现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开发区建设以及对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等,我们体制中的这些顽症并没有被制止下来,而且由于预期的作用,甚至可能出现了突击投资和大胆跟进的现象。因此,真正要下决心挤压下来的投资需求应该主要是那些没有效率的政府投资,而不能叫停那些迎合市场和赢利前景好的投资需求。
为什么治理过热投资重在治理银行?
如上所述,最近这几年,商业银行方面贷款能力的显著改善和地方上总是存在的旺盛的投资需求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共同引发了这次的投资膨胀,产生宏观上的经济过热的压力。如何化解这些压力,解决好过热压力的形成因素,主要取决于我们对当前出现的投资增长过快的趋势是否可以抑制住。这就涉及到宏观治理政策的选择问题。政策上最大的挑战是不容易找到最适时、最适合和最适度的政策。这好比用药,既要剂量得当又要用副作用最小的药。这非常不容易,需要多方面的智慧和经验。一般来说,在控制总量的膨胀问题上,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往往是最重要的手段。在美国或发达的市场经济里,“升息”往往是“金牌”手段。因为升息提高了融资的(机会)成本,有助于抑制投资需求和对信贷需求的过快扩张,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一旦解压了,货币当局可以再逐步降息或(和)采用财政和收入政策来恢复经济的增长。所以,在治理宏观经济波动问题上,通常央行(货币当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我们的经济,要化解掉这些通涨的因素,在短期似乎也只能想办法将投资需求过快的增长减慢下来,在这一点上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的问题与西方有所不同的是,第一,中国的政府体制不同于西方,我们可动用的调控政策除了货币政策之外,我们也有行政手段可以用于控制投资过热;第二,中国的投资需求几乎全然是依靠银行的信贷来支持的。这使得我们的宏观治理更加复杂了。例如,旨在抑制投资需求过快增长的紧缩性政策要么不怎么起作用(如提高利率),要么会在短时间里迅速增加银行的坏帐规模(如对在建投资项目的行政“叫停”)。但是,如果经济过热得不到及时的治理,以至于最终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不得不全面叫停时,银行的坏帐会更严重,规模也会更大。从上一次的经验教训来看,在不得不实行严厉的叫停政策之后,银行的坏帐大幅度地增加了,这在日后就为银行普遍出现的“惜贷”和过度谨慎的信贷行为提供了理由。其结果,紧缩政策之后可能就无法很快、很好地启动经济的投资需求,因为银行系统要花很长的时间来消化不良信贷,导致长时间的宏观“紧缩”。
因此,现在对中国的投资膨胀和经济过热的治理就应该充分考虑到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是要控制过快增长的贷款规模,因为贷款规模增长过快会导致银行潜在的风险急剧增加。但问题是,这些激增的贷款大部分是流入了房地产、钢材、水泥、电解铝等行业,因为这些行业的市场行情和预期盈利都不错,而一旦实行严厉的行政性紧缩和叫停后,这些行业的价格如果出现大幅回落,会导致这些目前尚好的项目变坏,使本来隐性的、或有的贷款风险变成真的呆账坏账,在短期急剧加大银行的风险。因此,简单的行政性叫停是要慎用的。
既然这样,在治理中国当前正在形成的经济过热时,我们就不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主要依靠央行的货币政策将治理的重点针对投资“需求方”去考虑宏观的紧缩政策,我们更需要“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进行严格的监管与风险控制的措施。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同时对商业银行进行信贷和信贷风险的监管,仅仅靠央行提高利率往往并不能很好地抑制地方的投资需求的增长。所以,央行提高准备金率往往就比提高贷款利率更重要,因为提高准备金率将治理的对象针对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的增长速度。在中国,可以不把提高利率的政策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去考虑,重要的是,既要将商业银行贷款的增长速度降下来,又要不至于大幅度增加银行的呆坏帐规模。
而要做到这一点,“银监会”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银监会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需要特别策略性地将治理的重点放在新增贷款方面,而同时指令商业银行对已经发放的贷款加强风险的监管。从现有出台的政策来看,对于已经开工或者正在建设的项目所发放的贷款,银监会的确加强了对商业银行在审查和批准贷款申请中的“窗口指导”的作用,银监会应该要求银行加强和加大对已发放信贷的跟踪和风险监管,防止因贷款申请审查不严而可能导致的不良贷款形成的风险。银监会于4月13日已经发出的“通知”也是旨在对已经发放的贷款进行清理和监督的一种努力。实际上,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本来是商业银行的惯例,但在中国,这样的信贷监管往往流于形式,得不到真正的贯彻落实。所以,在投资出现过热的情况下,这样的信贷风险管理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我想,我们要力争实现经济“软着陆”,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就需要避免从经济过热转变成通货紧缩。而现在的投资过热并不必然导致未来的生产能力过剩和更严重的通货紧缩。其实,通货紧缩的发生不取决于现在投资是否过热了,而是取决于治理过热的政策是否过了头,是否严重伤害了经济的复苏能力。在中国,只要治理的政策不严重改变银行的风险组合和偏好,银行就能够在日后继续为总需求的复速和增长提供支持而不是采取过度谨慎的“惜贷”行为。只要容易重新启动需求,尤其是对生产能力存量的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本来是可以由市场自身(如破产、兼并和重组)来消化的。因此,当前的投资过热会不会带来更加严重的通货紧缩,关键的问题是,现在的治理政策要避免我们上面谈到的不要在短期过于加大银行方面的呆坏帐和风险。尤其是,当前的通货膨胀还非常温和的时候,加强对商业银行的信贷监管和风险管理,我们完全可能用比较温和的办法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不仅如此,从加强对银行的信贷监管和风险管理方面入手来治理投资过热,还将从长远改善中国经济的健康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