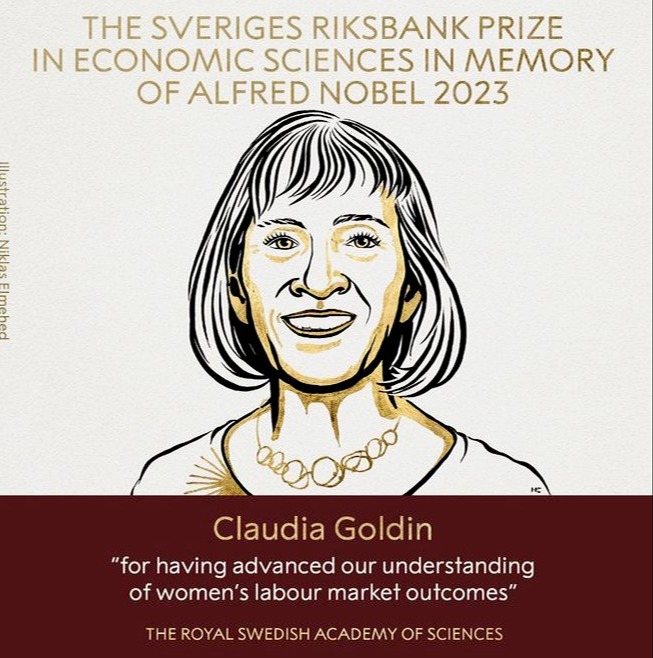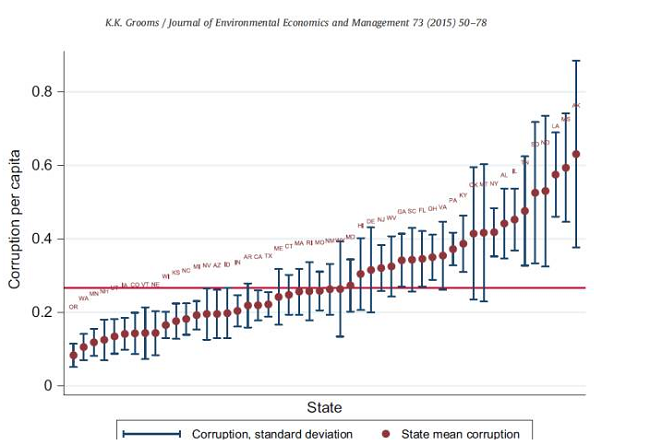美联储一百周年之际的改革法案
观点 · 2014-09-17
返回文/Simon Johnso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
要点总结
1.所有繁荣的工业化民主国家都有一个兼具独立性与民主问责的中央银行。过去100年间大量国家的经历反复证明了在委任的货币政策官员与获选政客之间设置一个缓冲区的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任何涉及制定与实施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官员必须最终,至少是间接地对选民负责。
2.有效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有如下的要求:
(1)固定任期,不会因为政策分歧而被解雇或排挤出局。例如在美国,这意味着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14年的任期。
(2)在时间紧迫的压力下可以做出日常决策的能力,并且没有遭到政府其他分支机构的否决的风险。
(3)有限的司法审查。举例来说,法院不能裁定美国(或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的利率被设定在了一个不合理的水平。
(4)预算独立——美联储的预算不来自于国会的拨款。
3.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需要在最大程度上免受党派或政治的影响。利率的设定不应该考虑到选举周期。
4.联邦储备系统中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同时监管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在《多德—弗兰克法案》之下)任何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的企业或活动。大型金融机构,尤其是那些被认为“大而不倒”的机构,经常反对对于他们活动的有意义的限制。他们尤其反对对于他们增加杠杆率(即拥有相对于他们持有的权益资本而言大量的总资产)的能力的限制。因为这些银行主管的收入一般是基于他们普通股的回报,并没有充分进行风险调整,这样的方式产生了大量预期的私人收入。高杠杆率还存在很大的不能被任何公司内化的负外部性。
5.自2008年以来,美国大型银行控股公司都拒绝制定了更严格的资本要求,更低的杠杆率上限以及其他改革的沃尔克规则。他们同时反对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对于衍生品的规则,并且他们继续反抗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一系列事件的改革。
6.美国长期以来都是通过任命专家来处理货币政策和进行金融监管,并受到相关政治家的监督(例如通过参议院的批准,出席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听证会以及服从重新任命)。这些专家的目标是由法律规定的且十分简单明确。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也采用类似的方式——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和美国的实践趋同,尽管赋予不同目标的比重在不同国家之间仍有很大差异。
7.这些专家需要有足够的应对能力。当经济与金融系统发生改变时,这些官员们必须及时合理地调整政策。
8.当下起草的美联储问责与透明法案(H.R.5018)将会过度限制官员全面并且及时改变经济与金融状况的能力。我在下面的第二部分会更加详细地阐述我的担忧。
9.美国的确拥有相对于其他领先的中央银行不同的关于货币政策的治理结构。在我们的联邦储备银行框架下,银行家们对这些联储的潜在影响力胜过总统——并且这些官员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任职(除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是常驻成员外,其他联储银行行长在委员会的任职采取轮流制)。相对于其他高收入国家,这种方式使得私人领域的银行家对于利率有更多的潜在的影响力。
10.第三部分的证据显示,如果国会想要增强联邦储备系统的治理能力,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将是最好的着手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是美国(乃至世界)最有权利的官员之一。他/她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副主席,并且在实施货币政策与国债管理(有效地代表财政部)上起到领导作用。他/她在决定是否对特定群体的投资人进行救助以及交易的谈判和细节条目时是非常关键的人物。纽约联储的行长是由总统任命的,并且需要得到美国参议院的同意。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运作不能被由金融机构推荐或选举产生的董事会所控制。
一.对于立法提案的具体评价
当前起草的美联储问责与透明法案有三个主要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对美联储的政策制定者施加压力,使他们遵从由国会规定的决定利率水平的货币政策规则,而不是允许他们基于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利率水平。这部分地可以通过在国会委员会指导之下的政府问责办公室(GAO)对美联储货币政策制定的审计来实现。
第二个目标是要求美联储公开银行常规压力测试的细节。第三个目标是要求美联储在草拟监管规则的时候,要进行特定的成本收益分析。
在当前的草案中还有其他的小变动,比方说关于在监督时必须由副主席提供证词的改动以及在进行国际谈判前须满足的要求的改动。
我将在下文一一讨论这些要点。
1.货币政策规则
现代央行十分强调关于目标和行动的清晰的沟通,美联储也不例外。但是立法提案却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前进,企图详细地制定决定货币政策的默认规则(例如由政策管制的利率水平),并为这些规则建立一些浮动范围狭窄且十分具体的标准。
提议的框架引发了以下具体的问题:
(1)当GDP的测算方法像其他规律一样更新或修改了的时候,将如何应对?
(2)在提议的新的政策指导规则中提到的“货币总和”指什么?
(3)在计算供参考的政策标准时,若实际GDP高于预测的GDP或者发生了通货紧缩(物价水平下降)将如何应对?
(4)所谓的“稳定物价”到底指什么?相似的,“长期最高自然就业率”又具体是什么含义?
政府问责办公室的审计机制在某些细节方面十分具体,并且看上去是专门设计出来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施压的。潜在的效果可能让人感到恐惧,会给富有成效的工作造成障碍,并带来更大的党派压力。
如果政府问责办公室发现实际政策与规定的框架不符,你怎么联邦储备系统的主席必须在7个立法日之内就这一点进行说明。
在整个立法提案中最不明晰的地方大概就是有关政府问责办公室的审计部分,其实列明“总审计长需要审计货币政策的实施”,并且必须“基于适当的国会委员会的要求。”此外,还有“国会委员会可以指定审计的参数。”
这会给货币政策制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审计的准标是什么?这些标准会在何时制定,又该如何制定?它们在不同的审计中是否会发生变化?这最终会导致任何利率变动都将受到调查吗?
这反应到金融市场的净效应,就是波动性的增加。预计会打压投资,使经济活动比本应有的水平更加低迷。
2.压力测试
最近几轮的压力测试成功检验出了资产负债表和大型复合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工具的弱点。
这些公司争论要求将所有压力测试要求的细节以及相关模型都提前公开,并且避开任何维度的数量分析。大型银行控股公司也希望迫使美联储全面公开他们的模型,以便他们的员工更有效地选择提交给压力测试的材料。
这里提出的立法方式并不具有吸引力,因为它可能会将压力测试从一个检验资本充足程度的有效工具变成没有信息量的打勾练习。更糟糕的是,如果大型金融机构可以找到投诉对抗美联储的方法,那么他们就可能利用这种方法来阻碍各种可能减小系统性风险的决策。
3.成本收益分析
新提案会带来繁琐的“成本收益分析”负担,就像业界企图施加给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这样的监管者的一样。像起草的那样,法案也会将诸如此类的成本收益分析施加给货币政策的决策过程。
任何像美联储一样良好运转的中央银行,都会考虑各自行动的利弊。并且美联储的高级官员会经常以演讲、证词或其他形式解释和辩护这些政策。
举例来说,在形成最近敲定的沃尔克规则的过程中(涉及美联储和其他机构),有很长一段征集意见的时期,并且出现了大量官员和业界之间的互动。
此处提案的成本收益分析将会减慢各种形式的规则制定的速度。尽管没有明确指出,这也可能会使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决策受到更广泛的司法审查。就像我们在其他监管机构身上看到的那样,这会加大有效并且明确地实施规则的难度。
这项法案同时规定监管者可能发现“没有监管”成为他们的首选。这与要求对特定事项进行监管的国会立法形成直接的矛盾。监管者需要做的是制定出如何实施国会要求的细节;而不应该是事后劝告当选议员什么应该出现在法律中。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在这个“成本收益分析”的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性。在典型的案例中,业界的代表写了很多评论,声称有各色各样的成本,虽然这些言论有时会带有大量的夸张成分。如果监管者不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些细节(毕竟这是游说的一种形式),他们就会被业界起诉。然而,如果监管者错误地站在业界这一边并且施加了十分微弱的或者无效的规则,社会公众一般情况下不会起诉他们,因为大众缺乏立场,哪怕实际上他们会从有效的规则上受益(如沃尔克规则,限制自营交易和其他形式的会损害经济的过度冒险,这些经济问题包括就业和其他对社会个体而言意义重大的结果)。
这种形式的“成本收益分析”因此成为了向业界倾斜的法律策略。目的就是制造潜在的技术缺陷,使得法庭可以认为美联储的规则制定得并不合理,或者没有充分考虑到来自业界的意见。就像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经验显示的那样,这减缓了监管的进程,并使得监管变的更加难以处理。譬如,没有引用受业界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并且这项研究并没有可靠的发现——就足以推翻一项规则(或者退回重新考虑)。
按照目前的解释,法院并没有评估成本收益分析的实质的专业能力或者授权。这纯粹就是制造一个程序上的障碍。
基于以上论点,这项法案的净效应或者说没有意识到的结果,就是增加繁文缛节和程序上的障碍,使得有效操作变得更加困难。这包括此处繁琐地指出的采用之后的所有形式的评估。增加对于这些文书的要求是保证官僚体系和政府规模以无效率的方式扩张的一种方法。对于中央银行业务来说这不是一个吸引人的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对物价稳定的潜在影响以及美联储稳定物价的能力却没有被提到,这不得不让人感到有点奇怪。
任何成本与收益评估都必须考虑到发生像我们在2008年经历的那种重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我们需要当心,不能对所有创造的工作岗位赋予相同的比重——比方说,如果这些工作是纯粹的寻租活动或者是大量不透明的政府津贴的后果,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它们可以被认为拥有更低的价值。
为了达到效率,中央银行必须保持一定的灵活度。应该任命顶级专家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必须有空间好好地执行他们的工作。
4.负责监管的副主席
《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负责监管的副主席需要出现在参议院的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与众议院的金融服务委员会,出席半年召开一次的委员会针对储蓄机构监督管理的成就、活动、目标以及计划的听证会上。”
新法案附加了一个要求,如果负责监管的副主席职位空缺,则其他副主席(或者主席)需要代替进行说明。这看上去并不是不合理。
我们的确需要对联邦储备委员会负责监管的副主席的职责进行改进。我们也需要这个职务上的官员去推行《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核心条款,包括让大型金融机构的“生前遗嘱”变成可以有效利用的工具,并且保证当大型银行控股公司面临破产时有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关于这点,我们需要设计针对主要由普通股构成的银行控股公司的融资结构。
5.国际谈判
如果美联储或者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希望进入国际谈判,新法案试图施加一个更长并且更正式的评估期。
考虑到跨境问题对于金融机构濒临破产的潜在解决方案的重要性,这样的要求会给可行制度的落实到位加大难度,也可悲地使得一些公司“大而不倒”的观念更加难以全面终结。
大型公司同时反对有效的跨境资本要求,特别是那些集中在杠杆率上的(即没有使用风险加权)。就像当下起草的那样,新法案将会协助大型国际银行拒绝合理的资本监管。更一般地说,针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国际标准正在逐步提高。业界决心要最大限度地减缓这个进程。
二.联邦储备系统与治理
当前起草的法案没有解决联邦储备系统治理中最重要的问题: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任命和职责。该问题的核心是一个不幸的时代错误——决定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成员的机制。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职员是由智慧的高度专业人士组成的,致力于让金融系统更加稳定。与此同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决定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各方面运转、包括决定董事会成员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似乎已经对于治理事务和这些会如何威胁美联储的独立性不敏感了。
就像其他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一样,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会和其他高级官员一起挑选潜在的董事会成员,所有任命都必须得到位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批准。罗得岛州的参议员Jack Reed在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辩论上讨论了这个问题:
尽管参议院法案包括我自己的提案都要求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由总统任命并得到参议院的同意,但是这项条款在会议期间被删去了。如果任命位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要得到参议院的批准,那么十分关键的、并且可能在金融危机期间对纳税人的美元负起更大责任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也必须服从于同样的公共认证过程。华尔街没有权利选择谁出任这样一个关键的职务。尽管最终的法案限制了联邦储备区代表持有股份的会员银行的A级董事参与这个过程,法案却允许了其他可能是银行家或者代表其他强大利益集团的董事投票选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我相信为了使这个职务更好地对纳税人负责,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
参议员Reed的分析仍然是正确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占据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在货币政策方面,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副主席和联邦公开市场操作政策的主要执行人;在监管方面,他/她是联邦储备系统在华尔街的耳目。他/她对于财政政策也很关键,因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是连接官方与政府债券市场的重要接口。这些权利是不在其他地区联储行长之间轮换的。
在《多德—弗兰克法案》之下,A级董事(代表银行家的银行家)不再参与地区联储主席的选举。但是B级董事是由银行家选举出的非银行家(代表公众)。以及纽约联储的C级董事,除了一些著名的例外,都和大银行走得很近。
C级董事应该更加独立于银行部门——他们的职责是监视整体经济,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这可以通过委员会改变成为C级董事的标准得以实现,尤其是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废除C级董事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这会让由银行家任命的B级董事得到更多的权利。
另外,如果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是由美国总统任命并由美国参议院确认,这会和国际惯例以及我们政治系统的其他方面更加保持一致。(完)
(原文选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之前的国会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