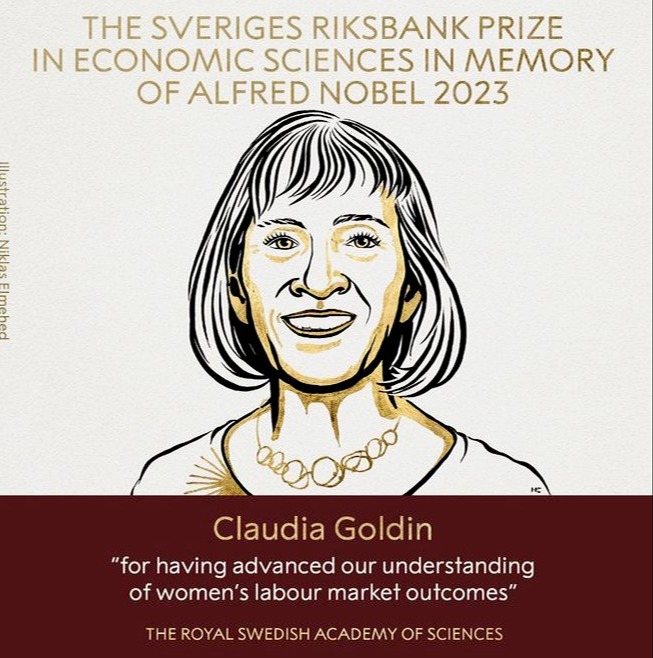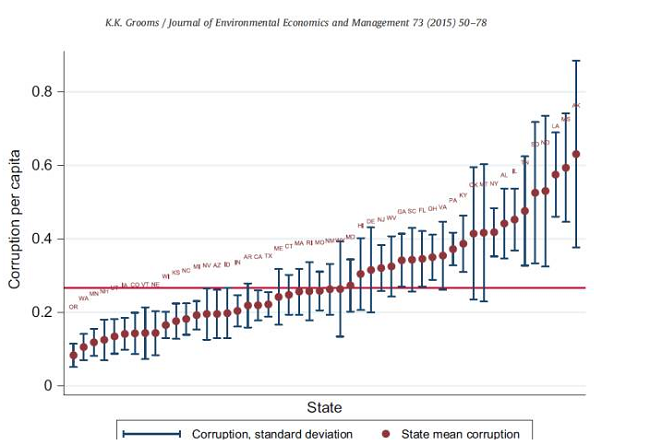张曙光:我的人生历程和学术生涯
观点 · 2009-12-16
返回
2009年农历9月8日是本人70岁诞辰,也是我从事经济学学习和研究50周年。《张曙光文选》的编选和出版,一方面是对自己学术生涯的一个小结,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我的家乡在陕西省长安县秦岭山脚下的偏远农村,距西安市50多华里。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两岁时父亲因病去逝,寡母勤劳刚毅,耕织皆是一把好手,但在传统社会,能够顶门立户,将我养大成人,教我读书成才,其所受的身体之痛和心灵之苦,是外人难以理解和体知的。先母1983年病故,生前母子身处西安和北京两地,我也很少尽人子之孝。对于母亲的养育之恩,我始终怀着深厚的崇敬和感激。
1959年,我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统计学专业,开始了经济学的学习和训练。在校期间,对我影响大的老师有何练成、冯大麟、吕其鲁三位教授。我的第一节政治经济学课是何老师讲授的,后来还听过他的多次报告,他传达孙冶方先生价值论的报告今天还历历在目。我一进校,就从“反右倾”运动的小字报中知道冯大麟和陈维满合作出版了《中国工农业协调发展问题》的著作,冯老师又给我们讲授《国民经济计划》课,因为培养了我这个“白专”典型,并支持和指导我报考研究生,文革中曾经受到冲击和批判;文革后曾任陕西财经学院院长,每次来京总要来家看我,并一起交谈。吕老师给我们教《国民经济统计》,当时因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而受到师生的拥戴,也成为我学习的榜样。
大学时期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我也因营养不良而患了浮肿,腿上一按一个坑,半天起不来。不过我的学习没有放松。当时时兴交际舞,很多同学星期六、星期天跳到午夜12点,我是个舞盲,也不感兴趣,这些时间是在图书馆渡过的。《资本论》就是在这个时候读的。
1963年大学毕业,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学校和老师鼓励我考研,帮我报名,给我时间复习准备。结果一举考中,一起录取的还有两位师兄弟杨圣明和李德华。专业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导师是杨坚白教授,副导师是董辅 、刘国光教授。谁知,专心致志学习了一年,接着就是不断的政治运动。1964年经济所批判孙冶方,我们几个来所不久的年青人被分派去监护顾准;1965年参加周口店农村“四清”;1966年研究生学习期满毕业,接着就是十年“文革”的浩劫和干校的劳动改造。在极左社会思潮的裹胁下,文革初期当过造反派,做过蠢事,中后期挨过整,被打成反革命,隔离审查达四年之久。1968年冬,我婚后一个月离家回京,第二天即被关了起来。我因失去了一切自由,音信全无,妻子在担心、屈辱和泪水中度日;后来可以给家人写信,但必须经过审查;干校时因病住院手术(阑尾切除)也有人监视和看管;大女儿满月时,我被允许回家看过一次,直到两岁多我才第二次见到她,她自然不认识我这个父亲,一见面,竟跟着她的表姐叫我“舅舅”。切肤之痛,深知自由之可贵。这也许影响到我今天的价值立场和人生态度。
1977年开始恢复业务,做的第一件工作是在鸟家培教授主持下,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学习《论十大关系》宣传材料”。实际做研究工作是1979年的事情。该年我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略论自负盈亏”,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至今也已30个年头。
1980年,为了推进经济调整,中央政策研究室组织编写《学习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参加者有林子力、刘国光、曾启贤、胡瑞梁、田光、肖灼基和我。具体任务有二,一是为《资本论》第二卷的每一篇写一篇解读文章,刘国光和我负责第3篇;二是对《资本论》第二卷进行删节,删去2/3。一方面,该书作为干部学习材料广为发行,另一方面,在编撰者中除我以外,都是文革前出道的名家,再加上为了配合这次学习,《经济研究》从1980年第5期开始开辟了一个“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专栏,约我就“学习《资本论》第二卷”连续写了三篇文章。于是,很多没有见过面的学人都把我当成了“老先生”。这就提高了我在国内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
我接受的是传统经济学的教育和训练。改革开放既是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批判,也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反思。随着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发展,我也经历了一个理论知识转型和研究范式转换的过程。80年代中期,我对传统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解释力发生了怀疑,这种怀疑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日益增长,于是开始学习现代经济学,更新知识结构。这是一个虽不能说是痛苦但也不那么轻松的过程。我原来学习的是俄语,英语是文革后听广播自学的,只能看,而且阅读的速度较慢。因此,我的学习方法有三,一是认真阅读当时翻译过来的著作,凡读过的著作,对其中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一定要搞懂弄通;二是主动与年青学者一起讨论和交流,虚心向他们学习。其中,与樊纲、杨仲伟等一起研究和撰写《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起了重要的作用。有朋友感到不解,曾经问我,你已经是研究员了,为什么总和年青人混到一起。三是读书和评书。应当充分肯定,我的知识很多是从书评中来的,这方面的文字也最多。在《评书论人和不同――学术书评卷》和《心交神往知与识――序文前言卷》中,我将对此做出交待。经过10年的努力,我基本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完成了知识转型和范式转换,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学术界,1994年开始撰写1999年出版的《制度主体行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反思》,就是这种学习和转型的结果。这时,一些未曾谋面的学人读了我的文章,又把我当成一个年青学者。从这套文集中,读者可以看到我的人生轨迹和学术道路。
我其所以能够完成知识更新和范式转换,也许与我对新事物的敏感和执着不如关系。就以换笔而论,90年代初计算机还是新鲜玩意,看到个别青年学者使用计算机写作,甚为羡慕,决心效发。1993年,有一个与美国学者萨克斯、胡永泰、史泰利等进行合作研究的项目,我与樊纲等去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作访问学者,花2000多美元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回国后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学会了五笔字形输入法,开始照着文稿用计算机“写”第一篇文章“关于地区经济差异的另一种解释”。敲了一半,就干脆扔掉文稿,边思考边输入,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写作方式。
认识到知识更新和范式转换必要性的人,也许不在少数。但真正能够认真实践,并实际完成和实现者很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有没有信心和决心,因为这样做必定是有成本的,而传统理论仍然有其市场和需求;二是能不能下这样的工夫,四、五十岁的人要做二、三十岁人做的事情,有些甚至是从头做起,不下一番苦功是完成不了的,不少人也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三是态度和方法,现代经济学的优势在年青人和留学者方面,对年青人和留学生的态度,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有人往往以已之长对其所短,瞧不起年青人;有人又感到年青人咄咄逼人,对自己名利地位构成威胁。这就妨碍了自己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努力,堵塞了更新知识的路径。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或者抱残守缺,在传统理论的框框内打转转,甚至借学术批评之名做一些政治批判和道德批判的事情,或者告老退休,离开学界。
说心里话,我进行知识更新和范式转换,并没有要在理论上做出多大贡献的雄心,只是想延长自己的学术生命而已。应当说,这个目的达到了。古语云,人生七十古来稀。在目前的国内,一个七旬之人,仍然活跃于学术界,还能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理论文章,如果不是独一无二,也属凤毛麟角,恐怕也找不出几个人。如果说,在年轻的时候还有对名利的景憧和追求,那么,到了后来,读书、思考、写作就成了生命活动的一部分。浸沉在这样的氛围中,整天忙忙碌碌,干自己所想和所好的事情,我的确感受到莫大的幸福和快乐。
在90年代以前,我的学术创作活动主要是围绕着本单位的重大课题进行的。曾先后参与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结构对策”、“2000年的中国”以及“深圳发展战略”和“海南发展战略”,“‘六五’经验总结”,“‘七五’国力预测”、“‘八五’改革大思路”、以及“体制变革中的宏观经济稳定”等项研究。这既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一方面,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理论界处于主导、甚至垄断的地位,在改革开放中的确起了打破理论禁区,推动解放思想的作用,政府也有很多重要课题都交给他们,另一方面,自己也比较年青,既有精力和热情,也需要学习和锻炼。90年代以来,自己开始独当一面,亲自主持了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诸如“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目标管理:宏观经济学”、“市场化进程中的宏观稳定”、“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核算”、“城市化背景下土地产权的实施和保护”等。无论是参与研究,还是自己主持,我都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坚持自己的理论立场。为此,不仅抵制和对抗过一些人的干预和插手,而且直接顶撞过我的顶头上司,甚至与之多次公开辩论,因而以“不听话”著称。其实,在现行体制下,虽不能说是所有领导,但绝大多数都不喜欢这种有独立思想的人。为此,我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最令人惋惜的是,当时我想出国把英语关过了,以便更好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但领导不给我这个机会。不过,教训也有,80年代中期在长江考察时,一位同仁执笔找我合作写了一篇观点有悖我意的文章,尽管我曾写信说明,但碍于情面,态度不够坚决,他拿去以我们二人的名义发表。此事令我追悔莫及,常常提醒自己。因而,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基本上都是自己动手,不愿依靠他人和自己的学生做事。难怪我的学生的同学对他说,“你们的老板(这里是指导师)真好,从不要你们做事,不像我的老板,我们不得不经常为他打工”。加之,看到一些同仁文章依靠学生出现的低级错误,更坚定了自己的做法。在这套文选中收入的文字,有少数是合作研究成果,也主要是我亲自执笔,由他人执笔的几篇,也是由我提出课题和思想,并最后修改定稿。
1993年,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聘为博士生导师,先后带的硕士和博士生有十多名。原规定可以招到65岁,带到68岁,但60岁时单位就一刀切要我退休,此后就没有在社科院再招收博士研究生。不过,编外弟子不少,很多不是我的学生,但在论文的指导以及做人处事方面,我的作用和影响也许不下于他的导师。毕业和工作以后,他们都与我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这里,我想简述一下我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做的事情。这也是我学术活动和人生经历的一部分。1993年7月26日,和茅于轼、盛洪、樊纲、唐寿宁等五位学者一起,与大象文化公司合作创办了天则所。这是一家创办较早且名实相符的非政府非营利机构。其宗旨就是要坚持和实践自由思想和自由讨论的学术理念,推动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实践。天则所创立以来,其活动有成功,也有失败,工作有波动,也有起伏,内部有矛盾,也有争论,但终究坚持了十多年,并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其他方面的事情暂且不论,仅就我所负责的学术工作(我一直任天则所学术委员会主席,1999-2002年任所长期间,名义上不是实际上仍然代管学术工作)来说,诸如,较早地组织举办了天则双周学术论坛,至今已经坚持了350多期,为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搭建了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现在各种各样的论坛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从1997年开始进行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每个季度提供一个分析报告,举办一次“宏观中国”论坛;现在宏观分析已经是群雄蜂起,诸家竞争。率先把案例研究引入国内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组织和主持了《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现已出版了五个案例集。另外还组织编辑出版了《中国经济学》系列14集和组织了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未来天则所如何发展,会达到一种什么地步,既取决于外部环境,也取决于天则理念的坚持和战略的选择,同时也与内部治理有关,这里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现在还很难预断。就我自己走过的道路来看,创办天则所既有很大的付出,也有不小的收获。
在我出道以后,曾经有好几个中央部委的研究单位请我去当官,拟任命我做研究院院长、研究所所长之类,并承诺解决诸如住房之类的实际问题。由于长期住在三里河名为两室实则一室一厅的住房内,架床叠桌,女儿从学校回家只能打地铺,唯一的希望是能有一张四条腿的床,夫人希望能够有一个朝阳的房子,朋友也劝我能够满足一下夫人的愿望。这些都是正当的要求和愿望,入情入理,毫不过分。但考虑到自己生性耿直,崇尚“独立意志,自由精神”,不愿趋炎附势,曲意逢迎,既不愿当官,也当不了官,同时深知到各个部门以后,就得围绕着领导转,用自己的笔去表达别人的思想,写文件,写讲话稿,没有了能够自由自主做学问的条件和环境,因而执意不去。甚至对夫人说,“你要是想让我少活几年,咱们就去当官”。因此,夫人批评我自私自利,我也无言以对,在这件事情上也许如此,我也是常人,并不那么高尚。到现在,在房子问题上,夫人的心愿仍未实现。这也是我非常歉疚的事情。
我其所以不去当官,也不去经商做企业,还有深一层的原因,虽然这些职业是社会必要的,也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但必须采取官方的立场和为营利而奋斗。而我则有着一个独立学人的情结,喜欢做一个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我只是想自由思想,自由言说,对任何事物保持一个批判的态度。至于我的观点和看法是否符合正统意识形态,能否被官方和业界接受和采纳,这是他们的自由和权利。
我的专业方向是宏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但实际所做的研究内容则比较广泛。根据研究工作涉及的内容和方面,我将《张曙光文选》设计为五卷,分别是
《入道求索未驻足――学术论文卷》,
《心交神往知与识――序文前言卷》,
《评书论人和不同――学术书评卷》,
《短章随笔辩是非――经济评论卷》。
《真实有用稻梁谋――研究报告卷》。
人常说,文如其人。从这些文章中,不仅可以了解我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态度,而且可以了解我的脾气禀性,为人处事。总之,可以对本人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当然,是非功过,任由大家评说,这套文选就是一个耙子。
本文来自: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论坛(http://bbs.efnchina.com) 详细出处参考: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17923&ID=411420
我的家乡在陕西省长安县秦岭山脚下的偏远农村,距西安市50多华里。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两岁时父亲因病去逝,寡母勤劳刚毅,耕织皆是一把好手,但在传统社会,能够顶门立户,将我养大成人,教我读书成才,其所受的身体之痛和心灵之苦,是外人难以理解和体知的。先母1983年病故,生前母子身处西安和北京两地,我也很少尽人子之孝。对于母亲的养育之恩,我始终怀着深厚的崇敬和感激。
1959年,我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统计学专业,开始了经济学的学习和训练。在校期间,对我影响大的老师有何练成、冯大麟、吕其鲁三位教授。我的第一节政治经济学课是何老师讲授的,后来还听过他的多次报告,他传达孙冶方先生价值论的报告今天还历历在目。我一进校,就从“反右倾”运动的小字报中知道冯大麟和陈维满合作出版了《中国工农业协调发展问题》的著作,冯老师又给我们讲授《国民经济计划》课,因为培养了我这个“白专”典型,并支持和指导我报考研究生,文革中曾经受到冲击和批判;文革后曾任陕西财经学院院长,每次来京总要来家看我,并一起交谈。吕老师给我们教《国民经济统计》,当时因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而受到师生的拥戴,也成为我学习的榜样。
大学时期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我也因营养不良而患了浮肿,腿上一按一个坑,半天起不来。不过我的学习没有放松。当时时兴交际舞,很多同学星期六、星期天跳到午夜12点,我是个舞盲,也不感兴趣,这些时间是在图书馆渡过的。《资本论》就是在这个时候读的。
1963年大学毕业,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学校和老师鼓励我考研,帮我报名,给我时间复习准备。结果一举考中,一起录取的还有两位师兄弟杨圣明和李德华。专业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导师是杨坚白教授,副导师是董辅 、刘国光教授。谁知,专心致志学习了一年,接着就是不断的政治运动。1964年经济所批判孙冶方,我们几个来所不久的年青人被分派去监护顾准;1965年参加周口店农村“四清”;1966年研究生学习期满毕业,接着就是十年“文革”的浩劫和干校的劳动改造。在极左社会思潮的裹胁下,文革初期当过造反派,做过蠢事,中后期挨过整,被打成反革命,隔离审查达四年之久。1968年冬,我婚后一个月离家回京,第二天即被关了起来。我因失去了一切自由,音信全无,妻子在担心、屈辱和泪水中度日;后来可以给家人写信,但必须经过审查;干校时因病住院手术(阑尾切除)也有人监视和看管;大女儿满月时,我被允许回家看过一次,直到两岁多我才第二次见到她,她自然不认识我这个父亲,一见面,竟跟着她的表姐叫我“舅舅”。切肤之痛,深知自由之可贵。这也许影响到我今天的价值立场和人生态度。
1977年开始恢复业务,做的第一件工作是在鸟家培教授主持下,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学习《论十大关系》宣传材料”。实际做研究工作是1979年的事情。该年我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略论自负盈亏”,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至今也已30个年头。
1980年,为了推进经济调整,中央政策研究室组织编写《学习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参加者有林子力、刘国光、曾启贤、胡瑞梁、田光、肖灼基和我。具体任务有二,一是为《资本论》第二卷的每一篇写一篇解读文章,刘国光和我负责第3篇;二是对《资本论》第二卷进行删节,删去2/3。一方面,该书作为干部学习材料广为发行,另一方面,在编撰者中除我以外,都是文革前出道的名家,再加上为了配合这次学习,《经济研究》从1980年第5期开始开辟了一个“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专栏,约我就“学习《资本论》第二卷”连续写了三篇文章。于是,很多没有见过面的学人都把我当成了“老先生”。这就提高了我在国内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
我接受的是传统经济学的教育和训练。改革开放既是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批判,也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反思。随着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发展,我也经历了一个理论知识转型和研究范式转换的过程。80年代中期,我对传统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解释力发生了怀疑,这种怀疑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日益增长,于是开始学习现代经济学,更新知识结构。这是一个虽不能说是痛苦但也不那么轻松的过程。我原来学习的是俄语,英语是文革后听广播自学的,只能看,而且阅读的速度较慢。因此,我的学习方法有三,一是认真阅读当时翻译过来的著作,凡读过的著作,对其中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一定要搞懂弄通;二是主动与年青学者一起讨论和交流,虚心向他们学习。其中,与樊纲、杨仲伟等一起研究和撰写《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起了重要的作用。有朋友感到不解,曾经问我,你已经是研究员了,为什么总和年青人混到一起。三是读书和评书。应当充分肯定,我的知识很多是从书评中来的,这方面的文字也最多。在《评书论人和不同――学术书评卷》和《心交神往知与识――序文前言卷》中,我将对此做出交待。经过10年的努力,我基本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完成了知识转型和范式转换,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学术界,1994年开始撰写1999年出版的《制度主体行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反思》,就是这种学习和转型的结果。这时,一些未曾谋面的学人读了我的文章,又把我当成一个年青学者。从这套文集中,读者可以看到我的人生轨迹和学术道路。
我其所以能够完成知识更新和范式转换,也许与我对新事物的敏感和执着不如关系。就以换笔而论,90年代初计算机还是新鲜玩意,看到个别青年学者使用计算机写作,甚为羡慕,决心效发。1993年,有一个与美国学者萨克斯、胡永泰、史泰利等进行合作研究的项目,我与樊纲等去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作访问学者,花2000多美元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回国后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学会了五笔字形输入法,开始照着文稿用计算机“写”第一篇文章“关于地区经济差异的另一种解释”。敲了一半,就干脆扔掉文稿,边思考边输入,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写作方式。
认识到知识更新和范式转换必要性的人,也许不在少数。但真正能够认真实践,并实际完成和实现者很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有没有信心和决心,因为这样做必定是有成本的,而传统理论仍然有其市场和需求;二是能不能下这样的工夫,四、五十岁的人要做二、三十岁人做的事情,有些甚至是从头做起,不下一番苦功是完成不了的,不少人也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三是态度和方法,现代经济学的优势在年青人和留学者方面,对年青人和留学生的态度,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有人往往以已之长对其所短,瞧不起年青人;有人又感到年青人咄咄逼人,对自己名利地位构成威胁。这就妨碍了自己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努力,堵塞了更新知识的路径。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或者抱残守缺,在传统理论的框框内打转转,甚至借学术批评之名做一些政治批判和道德批判的事情,或者告老退休,离开学界。
说心里话,我进行知识更新和范式转换,并没有要在理论上做出多大贡献的雄心,只是想延长自己的学术生命而已。应当说,这个目的达到了。古语云,人生七十古来稀。在目前的国内,一个七旬之人,仍然活跃于学术界,还能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理论文章,如果不是独一无二,也属凤毛麟角,恐怕也找不出几个人。如果说,在年轻的时候还有对名利的景憧和追求,那么,到了后来,读书、思考、写作就成了生命活动的一部分。浸沉在这样的氛围中,整天忙忙碌碌,干自己所想和所好的事情,我的确感受到莫大的幸福和快乐。
在90年代以前,我的学术创作活动主要是围绕着本单位的重大课题进行的。曾先后参与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结构对策”、“2000年的中国”以及“深圳发展战略”和“海南发展战略”,“‘六五’经验总结”,“‘七五’国力预测”、“‘八五’改革大思路”、以及“体制变革中的宏观经济稳定”等项研究。这既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一方面,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理论界处于主导、甚至垄断的地位,在改革开放中的确起了打破理论禁区,推动解放思想的作用,政府也有很多重要课题都交给他们,另一方面,自己也比较年青,既有精力和热情,也需要学习和锻炼。90年代以来,自己开始独当一面,亲自主持了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诸如“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目标管理:宏观经济学”、“市场化进程中的宏观稳定”、“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核算”、“城市化背景下土地产权的实施和保护”等。无论是参与研究,还是自己主持,我都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坚持自己的理论立场。为此,不仅抵制和对抗过一些人的干预和插手,而且直接顶撞过我的顶头上司,甚至与之多次公开辩论,因而以“不听话”著称。其实,在现行体制下,虽不能说是所有领导,但绝大多数都不喜欢这种有独立思想的人。为此,我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最令人惋惜的是,当时我想出国把英语关过了,以便更好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但领导不给我这个机会。不过,教训也有,80年代中期在长江考察时,一位同仁执笔找我合作写了一篇观点有悖我意的文章,尽管我曾写信说明,但碍于情面,态度不够坚决,他拿去以我们二人的名义发表。此事令我追悔莫及,常常提醒自己。因而,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基本上都是自己动手,不愿依靠他人和自己的学生做事。难怪我的学生的同学对他说,“你们的老板(这里是指导师)真好,从不要你们做事,不像我的老板,我们不得不经常为他打工”。加之,看到一些同仁文章依靠学生出现的低级错误,更坚定了自己的做法。在这套文选中收入的文字,有少数是合作研究成果,也主要是我亲自执笔,由他人执笔的几篇,也是由我提出课题和思想,并最后修改定稿。
1993年,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聘为博士生导师,先后带的硕士和博士生有十多名。原规定可以招到65岁,带到68岁,但60岁时单位就一刀切要我退休,此后就没有在社科院再招收博士研究生。不过,编外弟子不少,很多不是我的学生,但在论文的指导以及做人处事方面,我的作用和影响也许不下于他的导师。毕业和工作以后,他们都与我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这里,我想简述一下我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做的事情。这也是我学术活动和人生经历的一部分。1993年7月26日,和茅于轼、盛洪、樊纲、唐寿宁等五位学者一起,与大象文化公司合作创办了天则所。这是一家创办较早且名实相符的非政府非营利机构。其宗旨就是要坚持和实践自由思想和自由讨论的学术理念,推动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实践。天则所创立以来,其活动有成功,也有失败,工作有波动,也有起伏,内部有矛盾,也有争论,但终究坚持了十多年,并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其他方面的事情暂且不论,仅就我所负责的学术工作(我一直任天则所学术委员会主席,1999-2002年任所长期间,名义上不是实际上仍然代管学术工作)来说,诸如,较早地组织举办了天则双周学术论坛,至今已经坚持了350多期,为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搭建了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现在各种各样的论坛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从1997年开始进行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每个季度提供一个分析报告,举办一次“宏观中国”论坛;现在宏观分析已经是群雄蜂起,诸家竞争。率先把案例研究引入国内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组织和主持了《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现已出版了五个案例集。另外还组织编辑出版了《中国经济学》系列14集和组织了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未来天则所如何发展,会达到一种什么地步,既取决于外部环境,也取决于天则理念的坚持和战略的选择,同时也与内部治理有关,这里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现在还很难预断。就我自己走过的道路来看,创办天则所既有很大的付出,也有不小的收获。
在我出道以后,曾经有好几个中央部委的研究单位请我去当官,拟任命我做研究院院长、研究所所长之类,并承诺解决诸如住房之类的实际问题。由于长期住在三里河名为两室实则一室一厅的住房内,架床叠桌,女儿从学校回家只能打地铺,唯一的希望是能有一张四条腿的床,夫人希望能够有一个朝阳的房子,朋友也劝我能够满足一下夫人的愿望。这些都是正当的要求和愿望,入情入理,毫不过分。但考虑到自己生性耿直,崇尚“独立意志,自由精神”,不愿趋炎附势,曲意逢迎,既不愿当官,也当不了官,同时深知到各个部门以后,就得围绕着领导转,用自己的笔去表达别人的思想,写文件,写讲话稿,没有了能够自由自主做学问的条件和环境,因而执意不去。甚至对夫人说,“你要是想让我少活几年,咱们就去当官”。因此,夫人批评我自私自利,我也无言以对,在这件事情上也许如此,我也是常人,并不那么高尚。到现在,在房子问题上,夫人的心愿仍未实现。这也是我非常歉疚的事情。
我其所以不去当官,也不去经商做企业,还有深一层的原因,虽然这些职业是社会必要的,也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但必须采取官方的立场和为营利而奋斗。而我则有着一个独立学人的情结,喜欢做一个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我只是想自由思想,自由言说,对任何事物保持一个批判的态度。至于我的观点和看法是否符合正统意识形态,能否被官方和业界接受和采纳,这是他们的自由和权利。
我的专业方向是宏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但实际所做的研究内容则比较广泛。根据研究工作涉及的内容和方面,我将《张曙光文选》设计为五卷,分别是
《入道求索未驻足――学术论文卷》,
《心交神往知与识――序文前言卷》,
《评书论人和不同――学术书评卷》,
《短章随笔辩是非――经济评论卷》。
《真实有用稻梁谋――研究报告卷》。
人常说,文如其人。从这些文章中,不仅可以了解我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态度,而且可以了解我的脾气禀性,为人处事。总之,可以对本人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当然,是非功过,任由大家评说,这套文选就是一个耙子。
本文来自: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论坛(http://bbs.efnchina.com) 详细出处参考: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17923&ID=411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