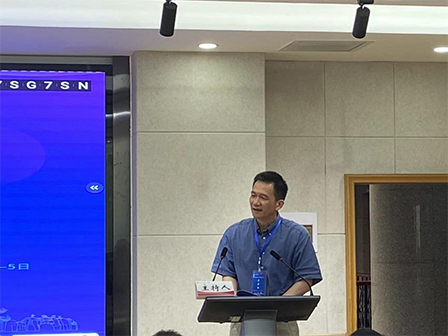“资本家的新天堂”:就业岗位?
观点 · 2014-06-27 00:00
返回(作者:本杰明•弗里德曼) 一 1963年,《纽约书评》首次出版之时,展现在美国人面前的是一片繁荣景象。这一年美国经济增长了大约4.5%,而前一年的经济增长高达6%,随后的三年平均增长率也超过了6%。在《纽约书评》...
(作者:本杰明•弗里德曼)
一
1963年,《纽约书评》首次出版之时,展现在美国人面前的是一片繁荣景象。这一年美国经济增长了大约4.5%,而前一年的经济增长高达6%,随后的三年平均增长率也超过了6%。在《纽约书评》面世当年的秋天,宏观经济的另一项重要指标,失业率仅为5.5%,此后一路走低,到1965年年中下降到4.5%,1966年底进一步降至约3.5%。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并不显著,1963年的消费者价格水平仅仅上涨了1.3%,这与1960年代前半期的均值水平相当。
最为重要的是,大部分美国人的收入增长超过了物价增长,这种状况在1963年之前已经持续了15年,之后又维持了10年。以现价美元计,美国家庭收入水平中位数在1948年为26500美元,1963年上升至41000美元,到1973年则高达55700美元。
即便如此,一些心怀隐忧的人还是表达了对美国经济未来长期前景及其对社会的可能影响的担忧。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当时就特别重视来自“自动化”的威胁(①参见J.E.Meade,Efficiency,Equality and the Ownership of Private Proper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该书主要是基于作者1964年春季在斯德哥尔摩的讲座稿。我特别感谢Anthony Atkinson推荐米德的著作。另外,该书的脚注在www.nybooks.com上可以查阅到。)。机器代替人工是几个世纪以来的一个美好愿望,同时也是一个隐忧之源。但是,在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贡献下,特别是1948年《控制论》出版之后,这一观念很快就流行起来。到1950年代中期,机器代替人工的场景还受到大众文化的青睐,弗雷德•威尔科克斯(Fred Wilcox)导演的经典科幻片《禁忌星球》(Forbidden Planet)就生动地幻想和刻画了这种奇妙的场景及其可能的可怕后果。
米德的洞见和威尔科克斯的电影一样吸引眼球。他所担忧的是那些在经济生产过程中被机器替代的工人如何谋生的问题。他问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
极其富有的人数将非常有限,盈利状况良好的自动化行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比例将会很小,这无疑会压低工资水平;同时,那些少数超级富豪迫切需要的劳动密集型商品与服务会有较大扩张,如此一来,我们可能重新回到一个充斥着管家、侍从、厨子和各种依附者的威权等级社会。对此,我们不妨称之为资本家的新天堂。
米德总结道:“在我来看,这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未来!”
二
担忧机器越来越多地代替男性与女性劳工所带来的潜在经济问题,米德并不是第一人。早在1810年代,在以内德•勒德(Ned Ludd)为传奇代表人物的纺织工人运动中,他们砸坏了新的自动织布机,以使那些技能不娴熟(因而工资也更低)的工人不至于失业。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经济增长明显受益于技术进步,生活水平也由此不断提高,技术进步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又一次“长波繁荣”,更是一场持久的社会进步。即使如此,对于科技进步,既有狂热者,也有反对者。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行的万国博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展示了新的进步时代的大量奇迹。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看到了一个“不是因为贫困而被奴役的”工人阶级。
但是,至少在英国和美国,情况变得更加美好。进入20世纪之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其他英国经济学家都在反驳马克思的预言,马克思曾经预言工人阶级无法享受生产率水平日益提高带来的成果。相反,马歇尔指出:“19世纪,工人阶级持续进步使得贫困和愚昧逐渐消失了”。的确,“对于智力工作需求的增长已经使技术工人迅速增加,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那些非技术的劳动力”,“而且部分技术工人已经过上了比上世纪大多数上流社会更加精致体面的生活”。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可能是对技术进步持最乐观态度的代表人物。在大萧条之前,凯恩斯继马歇尔之后又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预测英美两国的人均收入将可能每一两代人就会翻番,并推断,届时大部分居民将对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十分满意,至于要“解决”的各种“经济问题”,他们将会利用持续提升的生产率而不是调整个人消费来达到此类目的。
沿袭19世纪许多乌托邦式思想家的传统,凯恩斯也进一步臆想,在这样的环境下,社会将会淡化生产环节中的个人职能与其产出之间的关联性,因此,普通个体将在工作上花费更少的时间,但在日常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能力上则毫不逊色。结果是,凯恩斯所看到的主要问题,即如何消遣这些日益增多的闲暇时光,他称之为“普通人的可怕问题”。
凯恩斯曾经预言,从1929年开始的一百来年时间,人均总收入将增长4—8倍。如今80多年过去了,这一预言可能会实现。对于美国而言,凯恩斯的预测可能还有点太保守了。到2029年,美国人均收入增长预计可能超过8倍。但是,凯恩斯低估了人们希望享受更高物质生活标准的需求,同时,他也没有预测到经济总收入在分配上会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就业岗位也更加稀少。结果是,凯恩斯关于私人消费水平、工作努力程度、社会制度安排等方面的预测,在现实中很难找到相应的迹象。
三
今天看来,米德的担忧更有先见之明,至少在美国是如此。“创造就业”已经成为当前最紧迫的经济事务。为了能给本地居民(也为那些愿意从其他地方移入的任何人)带来工作机会,美国各个城市和各州都在相互竞争,例如,给予潜在雇主免税优惠期,降低土地租金,甚至放松监管。
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周期效应。1990—1991年经济衰退之后的反弹首度出现了“无就业复苏”。美国经济总产出在18个月内就超过了衰退之前的高峰水平,但是,总就业水平则花费了两年半才得以复苏。自此之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在2000—2001年的经济衰退之后,总产出仅仅在6个月内就迅速恢复,然而就业水平耗时4年仍未完全恢复。随后发生的2007—2009年金融危机,致使美国经济出现自“二战”以来最大的衰退,但是产出也只用了9个月就得以复苏。不幸的是,相比于2008年1月,2013年10月美国的就业岗位仍然大约减少了近200万个。
然而,美国的就业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周期问题。我们看到的特点是经济产出很快复苏而就业的复苏则耗时更长。那些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技术,例如以更有效率的方法组织生产流程、让工人使用更新和更好的机器以及用新机器取代人工与旧机器等,意味着比起以前,相同的产出水平需要投入的劳动力更少。因此,工人数量缩减的程度要看对其服务的需求状况,这首先取决于有多少人能够成为效率更高的劳动者,以及社会集体在多大程度上选择顺势消费比以前更多的商品。
诚然,技术革新通常不仅体现为以投入更少的劳动生产相同的产出。新技术也会带来新产品,在消除一些工作岗位(比如马鞍和马蹄开口制作的岗位越来越少)的同时,也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比如汽车制造和加油站岗位)。直到目前,制造原有产品的劳动力仍然数量庞大,加上那些生产新产品的劳动力,即使没有超过也与过去生产等量原有产品的劳动力差不了多少。
但是,这些反作用力之间的平衡没有理由要以这种方式呈现。不管是凯恩斯的乌托邦愿景还是米德的可怕前景,都不认为这种平衡会实现。在最近的25年里,这种平衡确实出现了偏向,工作岗位变得日益稀缺。
一个简单的原因可能是劳动力节约技术的革新步伐在加速。在1990年代中期,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其著作《工作的末日》(The End of Work)中强调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最近,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经济学家,埃里克•布林约夫松(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克菲(Andrew McAfee),用国际象棋的发明来比喻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当国王问这个发明者要什么奖赏的时候,聪明的发明者提出的要求似乎很简单:请在第一个方格放1粒米,第二个方格放2粒米,第三个方格放4粒米,以此类推,每次都翻倍直到放满第64个格子。国王爽快地答应了,他显然没有理解如此方式的奖赏,他不知道整个世界可能都生产不出这么多的大米。
在布林约夫松和麦克菲的比喻中,随着无人驾驶汽车和高品质翻译器的面世,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革新进入棋盘的另一半。尤其在美国,这一进程引领着信息技术领域的投资,日后可能的情景是生产出人们想要的各种商品与服务却不需要新增劳动力投入,产出规模会扩张,而就业岗位却不会增加。
四
技术的影响还有另一个重要途径,凯恩斯或米德都没有考虑到。随着新的电子通信技术在国际贸易中广泛运用,除了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安排传统的商品贸易之外,美国的就业岗位也在越来越多地“离岸化”,包括呼叫中心、X射线检查、退税准备和开展法律研究等。因此,即使美国人增加的消费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但也常常不能为美国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同时,对于那些必须在现场完成的低端工作——如米德所提及的管家、仆人和厨房女佣,在今天的环境下可能是门卫、园丁和医院的医护人员等——主要是那些数量稳定的非技术移民渴望从事的,这些工作的工资水平低,大多数美国人无法接受。结果是,即使额外的产出需要更多在美国的劳动投入,但也并不代表美国人的就业前景光明,至少并不是人们想当然的那样。
尽管造成这一事实的根源是我们的生产能力处于快速且持续的改善之中,但是,日益明显的结果是,我们不仅缺乏就业机会,而且收入不平等在扩大,同时赤贫在增加。自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完成他的著作《进步与贫困》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尽管他的许多分析已经不合时宜,但是他的书名所强调的矛盾在当今仍然适用。持续的技术进步使得产出的不断扩张成为可能,并且大部分都已经成为事实。但是增加的产出成果却日益为人口中极小部分人所享用,这些人绝大部分是收入水平处在金字塔尖顶的人。
在1973—1993年间,经过通胀调整之后,美国经济总产出增长了73%,人均增长了42%。但是,由于日益凸显的分配不平等,中位家庭收入的增长却不足4%。这个趋势在1990年代中后期虽然有所缓解,但是随后又依然如故。从2000年至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经价格调整后的人均总产出增长了10%,而中位家庭收入增长不足0.5%,以现价美元计,仅从67600美元稍涨至67900美元。到2012年人均产出几乎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但是中位家庭收入水平却降至62200美元,降幅超过了8%。
米德所担忧的图景日益明显,问题在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底部人群。凯恩斯则错误地认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中每个家庭所挣得的收入与所允许的消费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会被阻断。总而言之,从1973年至2012年,美国人均产出扩张了93%,但是美国中位家庭实际收入仅增长了12%。然而,有些人如米德所说的那些“超级富豪”们,他们的收入大幅增长。问题并不像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那样,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并不必然使每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大部分美国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几乎陷入了停滞,目前还没看到走出这种困境的曙光。
不仅如此,情况还有可能变得更糟。除了那些高技能和高学历的员工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之外,工资收入与财富收入——不管是通过持有股权、债券、房产或者是其他形式的资产获得——之间的平衡也正在发生变化。来自财富收入的份额占比已经创出历史新高。但是,财富持有的集中度远远高于劳动收入,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财富收入的占比日益提高,这将会进一步扩大总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不管工资结构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更甚的是,那些拥有大部分财富的人往往同时也是那些工资收入最高的人,于是这两股趋势在此汇成了一股洪流,而且更为糟糕的是,美国的税制使得工资收入的税负要远高于股息或资本利得的税负。于是,我们看到下面这组数据也就不足为奇了:2013年8月刚出炉的数据显示,2012年10%的美国人获得了整个国家一半以上的收入,再创历史新高,同时最富有的1%的人大约获得了其中的一半,或者整个国家收入的23%。
五
未来之路通向何方?在科技发展的进程中,对于那些无数“受损者”而言,其中至少有一些人可能会怀有勒德派分子那样的动机,不过没有人会阻止技术进步。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米德的可怕预期。最简单的答案一直以来都是市场化的解决方式:允许工资,特别是最低工资水平下降,直至劳动力市场最终可以吸收每一个愿意工作的人。这条路径将会以各种可能性造成不平等问题的恶化,但是,在理论上,每个愿意工作的人都能获得一份工作。遗憾的是,工资需要缩减的幅度并不是美国广大工薪阶层所能接受的。
更严格的边境。市场化解决方式的一个变种是放缓低技能工人移民美国的速度,也有可能会出现反向的移民现象。一个熟悉的说法是,美国人不会接受诸如此类的工作,言下之意是现在这类工作的工资水平太低了。如果没有那些愿意从事修剪草坪、油漆房屋的外国移民,这些服务的价格将会上升。一些房产主人将会自己修剪草坪,一些房子可能也不会粉刷一新(至少不会像现在那么平常)。如果草坪修剪工和房屋油漆工的工资上升,就会有更多的美国人愿意从事这类工作。更高的工资将会增加这类工作的吸引力。然而,大部分证据显示,移民进入对低端工资的压制作用是温和的:大致是9%左右,很可能还要更低。
“米考伯先生”策略。以前美国人经历了数次长期的经济停滞,但无一是永久性的衰退。有时候经济反弹是技术导致的,例如,由于发现了新的金矿以及黄金提炼技术的改进,对1880年代和1890年代初期的世界性经济萧条的终结大有助益。但是,主要技术突破的进展是非常难以预测的,尤其是难以预测一个具有足够力量来颠覆当今趋势的技术革新。
有些时候,终结经济停滞的东西并非是我们所期望的。在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的就业状况直到1943年才恢复至大萧条之前的水平,而当时全国有900万男男女女成为了军人。不管是通过战争还是技术突破,或者其他戏剧性进展,对于一个乐观者而言,总会有些东西使得繁荣“迟早会到来”,这甚至让我们可以暂时相信当期的勒德主义者是正确的,而历史总是证明他们是错误的。然而,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况且没有任何明确的经济规律证明它还会如此。
教育。一个司空见惯的事实是上一代的技术革新所创造的很多技能在当今的劳动力市场来说是没有多少价值的,相反可能增强了其他人的价值。大部分经济学家相信这个趋势是导致美国不平等恶化的最重要的单一因素。对此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大学生比高中生、高中生比辍学者的工资优势日益扩大的现实。毫无疑问,更多和更好的教育是很多年轻美国人的经济成功之道,也是美国经济总体上具有更高生产率的源泉。但是,时至今日,美国新毕业的大学生(更不要提及那些新毕业的律师和美容店技师们)面临非常糟糕就业前景的难以计数,他们甚至对于偿还教育贷款的预期都变得很渺茫。一个非常坦诚的评价是,我们可能已经走到了一个漫长时代的尽头,这可能已经不是一个可以依托教育的时代了。我们都知道,不管是对于个人还是整个经济而言,教育曾经是解决就业和生产率问题的万能钥匙。
收入共享。由于紧迫的问题是基本的生活标准,即人们能够消费的水平,那么我们在制度上如何去匹配工作的人与不工作的人?毕竟,事实上有一些人选择比其他人工作更多,或者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能力,或者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加富有。这些现象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麻烦的是不同人的生活标准的差异所导致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制度体系。许多工作的人(一般称为“成年人”)是在抚养其他不工作的人(一般称为“儿童”)。就既有的情况来看,这个制度体系大体上运行良好。同样的情况是,与最近这几十年相比,美国过去获得报酬的工作人口的比例明显偏低。由于赚钱养家的人(丈夫)与没有工作的人(妻子)很好地配对组合在一起,这个制度体系在过去能够运行良好。但是,如今这种安排已荡然无存,而且不会复返。今天成年女性的工作参与率已经高达59%,而男性的参与率是71%,两者相差已经不算太大了。
对收入共享问题的另一种考虑正是凯恩斯明确给出的假设,也是米德所深思的:即显著弱化每个家庭的收入与其所允许消费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如今,那些混乱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计划,以及政府向所有居民提供的免费服务(最为重要的是,到高中都是免费教育),在解决这些需求方面已经走得较远了。但是,公众日益明显的不满显示出,他们没能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不了由于收入停滞和不平等加剧所导致的压力。与此同时,在美国现行政治体系下,显著扩张社会福利体系,甚至对低收入工作进行工资补贴(采用工作福利而不是社会福利),几乎不具有可操作性。一些经济保守派人士曾经倡导的“按人头拨款”(Demogrants)——政府向每个人进行转移支付,不考虑收入——如今也没有人感兴趣了。
六
不管采取何种策略,目前最为紧迫的是让美国经济重回良性轨道,例如,重归《纽约书评》面世之时,或者更近的1990年代中后期,或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十年,这不仅使得经济总产出大大扩张,而且会提高大多数美国家庭的生活水平。这一诉求非常紧迫,原因不仅在于经济层面,还有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所表明,经济状况的改善通常会带来政治和社会的进步,反之亦然。如今“便秘式”的政治,正侵蚀着我们公共生活的礼仪文明,政策辩论中的慷慨美德也已消失不再。任何时候,只要我们大部分人失去了勇往直前的信念,没有了重新站起来的乐观精神,这些可预见的病理现象就开始显现出来。不过,今天所见的这些恐怕还只是初露端倪。无论身在何处,旷日持久的经济停滞已经让大部分美国民众感到越来越糟。
而且,如果采取与米考伯先生不同的应对策略,政治僵局都会使我们更加难以实行任何我们所需要的政策。因此,危险的是形成一个自我增强的均衡,经济衰退导致政治体系失灵,反过来又阻碍摆脱经济泥潭。而且,很多理由完全与政治阻碍无关,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教授预期未来美国生产率提升的步伐比过去更慢一些,因此总体上收入的增长也会更慢,他的潜台词是,在总收入的分配竞争中的大多数“受损者”,所面临的愈益恶化的收入停滞问题将会有所缓和。让生产率提升速度变慢的部分原因,很可能是目前还看不到有什么能够像以前的蒸汽机、铁路、电气化、内燃机、飞机,甚至是家里的水暖卫生设备等那样带来全局性改变的科技创新。而且,根据戈登的研究,我们还必须面对一些迫在眉睫的不利因素,例如,当前迫切需要解决包括经济增长导致的气候变化和其他的环境问题等。
毋庸置疑,像布林约夫松和麦克菲等技术乐观主义者会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事物的新苗头,他们认为数字化革命不仅会加速创新的进程,也会提高生产效率。但是,不管是美国人找工作所面临的困难有多大,还是美国人的工资是多么不平等,抑或是我们的总收入中不知有多少落入了资本家而不是劳动大众的口袋里,或者还有随之而来的政治和社会的堕落后果,无论我们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目前国家所陷入的困境,首要的是应该坦诚地认识到这种困境究竟是什么。
(郑联胜 译 董裕平 校)
Benjamin M.Friedman,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William Joseph Maier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