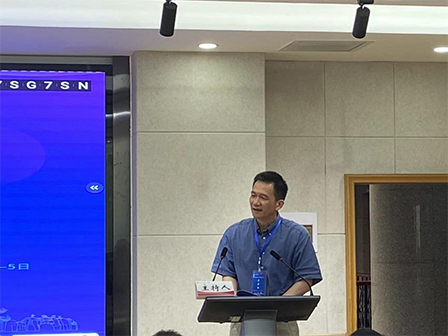向法国取经
观点 · 2009-03-06 00:00
返回这场痛苦的金融危机挑战了所有发达国家政府的正统经济学说。对平衡预算的长期信念遭到抛弃。在欧洲,稳定与增长协定已从视线中消失。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黄金法则已被熔化掉,与祖传银器一道卖出。 但西方中间偏左和中间偏右政府的政治计划遇到了更大的挑战。...
这场痛苦的金融危机挑战了所有发达国家政府的正统经济学说。对平衡预算的长期信念遭到抛弃。在欧洲,稳定与增长协定已从视线中消失。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黄金法则已被熔化掉,与祖传银器一道卖出。
但西方中间偏左和中间偏右政府的政治计划遇到了更大的挑战。在经济领域,他们能够回过头去求助于凯恩斯(Keynes),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新财政现实主义寻求智力支撑。从政治角度而言,解释政府的新作用更为困难。政府应在哪个领域进行干预,如何干预?公有制在短期内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最后会如何?目前的状况是否失常,或长期而言,我们是否需要考虑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建立新的社会契约?在英国,我们是否正见证着撒切尔-布莱尔主义(Thatcher-Blairism)的临终痛苦,如果是这样,是什么野兽正蹒跚走向威斯敏斯特去投胎?
当然,其它国家也面临着类似问题,但环境不同,其后果对现有秩序的威胁也没有那么大。华盛顿出现了一种名为“变化”的新意识形态。它可能需要充实内容,但已彻底脱离了布什(Bush)学说。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不需要像布朗不得不做的那样,努力协调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与过去的做法。无论如何,美国人民对意识形态不那么感兴趣。
在欧洲其它国家,政府转向关于政府角色的新说辞要更为容易。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奇(Nicolas Sarkozy)更像是一个实干家,而非哲学王。确实如此。但在他的背后和周围,以法国总理弗朗索瓦•菲永(Fran?ois Fillon)为首的政府官员正在构建新的说法。对于菲永而言,这场危机是创新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定义戴高乐主义(Gaullism)的一个机会。在今年1月在巴黎发表的一次吸引人的演讲中,他将其称为“经济效率、资本主义和社会公正的综合体”;接着他用戴高乐将军应该会喜欢的词汇,将其称为“对面对历史简化和破坏力量的人类状况的一种看法”。巴黎的宴会上永远少不了关于人类状况和命运力量的辩论。
但菲永的戴高乐主义也具有实用性。他对“政府的回归”和采取重大经济决策的必要性进行了渲染,回顾了前戴高乐派政府在核能和高速列车领域做出的战略选择。因此政府在经济中的新角色非常适合他。
德国人的挣扎更痛苦。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政府很难认同有必要出台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但与英国保守党相比,承诺共决权(工人拥有董事会席位)和社会对话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更能适应干预的角色。上周,德国内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发表了一次发人深省的演讲。他描述了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开放社会”(open society)与联邦及地区政府持续的、带有强烈地方主义和多样性色彩的正面角色之间的和谐共处。例如,公共部门应培育致力于小企业和零售客户的地方银行。
在英国,保守党和工党都在努力重新定义其对政府和市场的态度。关于监管的各种论调(更多监管、更少监管、放松监管、轻度监管),均无实质内容。两党都不喜欢国有化这个字眼,实际上多数选民也不喜欢。法国和德国能够回忆成功的国有企业,但我们很难记起政府涉足工业或金融何时是一个解决方案,而非问题。
因此,在意识形态的真空里,我们的政治目前已筋疲力尽。这可能很危险:这是在邀请极左和极右势力兜售他们带骗人的确定性。我们听说在政府内部,两派人正在进行辩论,一派人希望从令人遗憾的短期必要性的角度来论证政府的新角色,另一派则认为需要从长期、积极的角度重新定义。最近还出现了第三条路,英国商务大臣曼德尔森爵士(Lord Mandelson)没有发表的书面演讲中对此进行了阐述:在当前环境下,选民对新的政治愿景不感兴趣。政府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随时准备收拾衰退的残局。
我怀疑这是否可行,我认为,工党和保守党必须找到一种新方式来谈论政府在陷入困境的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根据菲永有利于自由贸易的定义,英国版本的戴高乐主义可能会让人乐于接受。英国保守党领袖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可能认为,前财政大臣肯•克拉克(Ken Clarke)的拉夫堡选区就相当于英国的科隆贝双教堂(Colombey-les-deux-Eglises)——上世纪50年代,戴高乐就在此等待着重返政坛的召唤。布朗认为也许是布鲁塞尔,因此把曼德尔森爵士从那里召回。然而,迄今为止,任何一位回归的英雄都没有提出新的哲学。
我们可能需要更为明确地从法国人那里借用经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总理们都不会坚持很长时间,特别是在他们成功且受欢迎的情况下。菲永的妻子是威尔士人,他在英国有强大的人脉。在英吉利海峡的这一边,第二份工作可能正等着他。
本文作者是伦敦经济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