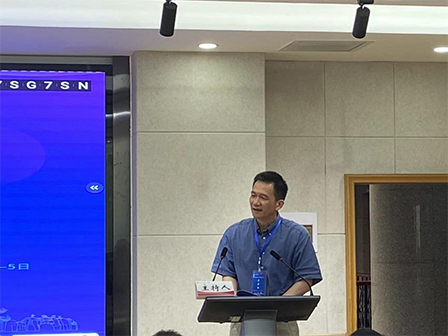左右之间:关于社会转型路径的思考
观点 · 2009-02-04 00:00
返回今年年初,我应邀在一个博士生讲座上演讲。当我讲到顾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追问,即沿着1789~1870~1917的道路进行革命的国家,为何会在胜利后从理想主义转化为专制主义时,推荐了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作为研究“...
今年年初,我应邀在一个博士生讲座上演讲。当我讲到顾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追问,即沿着1789~1870~1917的道路进行革命的国家,为何会在胜利后从理想主义转化为专制主义时,推荐了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作为研究“九三年”雅各宾专政的参考。不久,一位主持讲座的朋友郑重向我推荐林达的另一本书《西班牙旅行笔记》。我急忙找来这本书,一上手,就完全被它所讲述的西班牙几个世纪寻求民富国强之路的历史所吸引住了,不能不一口气读完。的确如我的朋友所言,这本书精辟而生动的阐述,将纷繁的人类历史变迁娓娓道来,展现出人类进步是各种社会力量抗争之后,达到一个暂时的平稳,再走向下一个冲突。从19世纪末期开始,西班牙经历了近百年的坎坷曲折。剧烈的社会冲突、民族分裂、内战、专政和杀戮,只是“在一次一次冲突之后,汲取了惨痛的教训,才告别了血腥,告别了专制,走到今天。”
林达讲述的西班牙故事对中国有意义吗?我的回答是肯定无疑。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好像一直在反复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问题。公元前209年各路草莽英雄怀着对秦王朝残暴统治强烈的义愤揭竿而起,推翻了暴秦的统治,然而这种革命并没有带来它曾经允诺的公平世界,而是“彼可取而代也”,“打倒了皇帝做皇帝”, 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一次又一次地轮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确切地说,给我们带来了顾准所说的“1789~1870~1917这股潮流”。当时我们许多人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中国革命取得胜利18年后的1967年,当顾准目睹“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重新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问题。
对于1789~1870~1917这条激进的革命道路为什么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还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潮流的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独裁、恐怖杀戮等来实现这一目标。继顾准之后,還有不少学人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乃至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了全方位的探索和破解。
《西班牙旅行笔记》提供了新的佐证。它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是: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林达用西班牙近代史证明,在大的社会变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观点分歧双方温和派的结合。如果不是这样,只要—方出现极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他自己的极端派,如果两边的温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渐被边缘化,社会就会被撕裂而趋向极端,而在两个极端之间的震荡,“不走到絕路不会回头”。这就是西班牙从18世纪初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以来多次上演过的悲剧。就拿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这次轮回来说,正像《西班牙旅行笔记》的作者告诉我们的,在1931年建立第二共和国的初期,虽然西班牙存在左右两派,但是两翼的温和派之间存在着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等最底线的基本共识。它们之间的分歧,无非是一个主张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另一个主张共和形式的民主制。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即使这种分歧不能通过和平协商来加以消除,也可以由选民用选票来决定,谁应当上台,谁应当下台。可是,当社会矛盾被激化,左右两边的极端派拉走了几乎所有的民众,国家分裂成了完全没有基本底线认同的两半,加上国际上德意和苏联两大集团的支持和挑动,分歧只能用全面内战的武力解决,最终以极右派将军佛朗哥的白色恐怖和40年独裁统治作为结束。
如果左边的极端派取得胜利那又如何呢?恐怕也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就像顾准所指出的,不论个人品质多么崇高,当1789~1917传统的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西班牙左派还在政权存亡未卜的内战时期,就在莫斯科的操纵下展开了极其凶残的内斗。林达为我们讲述了曾经是英国著名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作为国际纵队的一员参加西班牙内战的故事。满怀革命激情的奥威尔在国际纵队的列宁营中亲身目睹和经历的,是左翼阵营内部以“保卫人民主权”和“肃清内奸”为名进行的残酷斗争乃至人身消灭。他由此痛切地认识到极权统治以公众意志的名义恣意侵犯个人自由的极端危险性。这—经历,使他创作出对专制主义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无情鞭鞑的世界名著《动物庄园》和《1984》。
如果说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是一场旷世悲剧,1975年佛朗哥去世、卡洛斯国王加冕后,西班牙迅速“回归欧洲”和走向民族复兴则堪称现代奇迹。奇迹之所以能够发生,首先要归因于有关各方,包括出身于佛朗哥集团的新首相苏亚雷斯,共产党的领袖、当年在内战中负责马德里秘密保安工作的卡利约和社会党的领导人冈萨雷斯,他们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汲取了教训,共同参与了民族和解、民主转型和西班牙复兴的进程。西班牙共产党的老领导人伊巴露丽和新领导人卡利约早在佛朗哥死前多年就开始反思,并在斯大林去世后率先提出了“民族和解”的口号。1974年接任社会党领袖的冈萨雷断大幅度地修正了传统社会党的纲领,放弃了完全摧毁旧体制的革命纲领。而从佛朗哥的青年运动领袖出身的政府总理苏亚雷斯,也早已认识到西班牙进行民主转型的必要。再加上开明的年轻国王卡洛斯一世以高超的政治技巧从中斡旋,占了主导地位的右派温和派和左派温和派都能够采取理性态度进行协商和博弈,为共同的利益达成妥协,使西班牙得以渡过重重风波,在佛朗哥死后短短几年,就实现了民主转型,踏上复兴的道路。
其实中国人在最近一个半世纪谋求国家富强的途程中,也有过和西班牙人相似的某些经历。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政界、学界、企业界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在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国家这一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开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经济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在国际上,中国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于这些矛盾的由来作出了不同的解读和提出了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突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防止这种悲剧的关键在于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们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讨论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在讨论中,人们可以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是应该支持他发表自己的意见。只要不是谩骂、不是无中生有,一切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立论都应该受到欢迎。我现在感到特别担忧的是,如果匡救时弊的措施只是停留在宣言和承诺上,而实际的改进鲜有成效,各种极端的力量就会趁势而起,动员目前显得愈来愈不耐烦的民众,导致社会的动乱。
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旧的社会结构的产物,而不是不可改变的。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
旧中国社会和欧洲中世纪相同,是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社会:它的一头是大量的贫苦农民,另一头是少数权贵,中间阶层或称中产阶级力量即市民的力量十分薄弱。在这样的社会里,矛盾容易激化,政治诉求也容易趋向极端,在传统中国的专制制度下,暴君的残暴统治激起农民暴动推翻旧皇朝,农民当政后又或迟或早变成新的暴君,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了“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的周期更替。在欧洲中世纪后期,市民阶级和知识阶层开始壮大。在新的社会力量的孕育下,首先发生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这些促进社会进步的思想解放运动:接着发生了建立全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的革命变革。到了现代经济发展阶段,技术专业人员和经营专业人员的作用变得不可或缺,而且人数也越来越多。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中国也进入了这个过程。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包括各类科研人员和学校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和技工、中高层经理人员和一般公司职员、医护人员以及政府等公共机构的职员的队伍正在迅速壮大。这批人是工薪阶层中更多地具有现代文化技术知识的部分。他们追求的是经济生活和政治环境的改善和稳定,与社会弱势集团有着共同一致的根本利益,是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所可以依靠、也必须依靠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