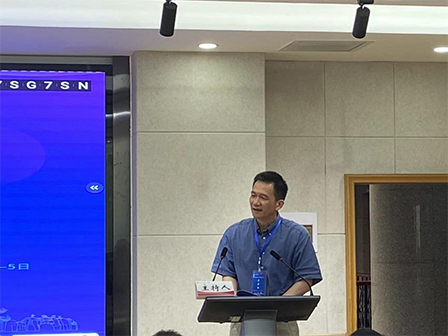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由来(结束篇)
观点 · 2008-10-24 00:00
返回中性政府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正在被一股股或明或暗的力量所蚕食,为了制衡它们,政府需要从寻求基于表现的合法性转变为寻求基于表现的合法性和基于程序的合法性的结合,其实质是使民众的参与更加制度化 本文连载至今,...
中性政府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正在被一股股或明或暗的力量所蚕食,为了制衡它们,政府需要从寻求基于表现的合法性转变为寻求基于表现的合法性和基于程序的合法性的结合,其实质是使民众的参与更加制度化
本文连载至今,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有赞同和鼓励的,但更多的是不赞成和指责谩骂。我感到有必要重申写作本文的初衷。当开始思考中国三十年经济增长的经验时,我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中考察——这里的“世界”不仅包括发达国家,而且还包括发展中国家。
一般而言,人总是更愿意和比自己生活得更好的人比较,此时难免要生出很多的不满。然而,不要忘记,发达国家也经历过和我们现在类似甚至比我们更糟的历史(想一想《雾都孤儿》里描绘的伦敦吧)。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有美国等最发达国家的二十分之一强些,中国的GDP总量可望在2035年左右超过美国,但在人均收入方面,中国赶上美国遥遥无期。我们还只是一个刚刚迈入中低收入门槛的国家,还是一个穷国。
以这样的眼光来看中国,我们就会发现,在过去三十年里我们比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做得更好。三十年的时间不算短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应该有这个自信,即中国所走的路,是一条正确的路。事实上,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一百七十年的历史,是世界由古代社会走向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一部分。西方也经历过漫长的古代社会,只不过它早于我们觉醒,但也仅此而已。
由此也引出本文最后要讨论的问题,即中国过去三十年高速经济增长对中国未来的意义。过去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中性政府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正在被一股股或明或暗的力量所蚕食,而这些力量又内生于过去三十年对维持中性政府做出了贡献的种种努力。这些力量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起来,主要是由于我们的体制本身缺乏制衡机制,从而不能防止事物的单向运动。
中国能够在过去三十年里维持一个相对于社会的中性政府,很大程度上和中国共产党把经济表现作为合法性的来源有关。然而,也正是因为过分强调了经济增长,问题逐渐显现出来,经济改革释放的动力渐渐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增长共识渐渐演变成一种片面追求增长而忽视人类生活其他方面的成见,这些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不仅本身是人类终极追求的一部分,而且还会影响到长期经济增长。
片面追求增长的做法、或“增长习惯”有下面一些负面后果。
首先是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尤其是农村和城市的差距以及内陆和沿海省份的差距。收入差距不仅是经济规律使然,有可能是特定人群获取收入的能力被剥夺的一种表现,在这里,政府针对农村移民的政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沿海省份需要内地移民来发展地方经济,但那里的政府政策仍然不利于移民的定居。尽管近些年来直接的歧视少了很多,但户口制度的持续存在仍然剥夺了移民定居的权利。其中一个后果就是移民的子女缺乏合适的教育机会——一个城市是否为移民子女提供教育是有选择的,要视当地经济发展的目标而定。由此,增长共识损害了移民工家庭获取未来收入的能力。
其次导致政府对民众权利的侵害,并可能会破坏一个保持活力和人道的社会所必需的社会纤维。对于政府官员来说,为了经济增长这些代价是值得的,他们认为,少数人付出的代价带来了多数人的更大收益。但是,这样的计算忘记了这些代价不是孤立的,而是会给社会带来更多方面的影响。例如,由于旧城区被高耸的办公楼和居民楼取代,中国的大部分城市已经变得无法辨认;与此相伴的是,城市失去了它们的社会内涵和特色文化。我们在犯着一个和1950年代后期破坏北京旧城同样的错误。
第三个负面影响是环境的恶化。中国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全国超过三分之二的河流被污染;沙漠离北京越来越近;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土壤不断流失。在山西,一个以煤炭采掘为主的省份,环境恶化引发的冲突不亚于一场“环境战”。很多环境退化,如沙漠化、水土流失和地下水的污染,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永久性的。
要改变以经济增长为单一目标的增长模式为关注人类发展各方面的多目标发展模式,势必对国家治理模式提出新的挑战。
中国政府能够在过去三十年里保持中性,还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弱化党的意识形态色彩,并在组织上从“党国”体制转变为“国党”体制。然而,完全失去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追求,党作为一个组织也面临一系列的危险,其中最严重的,是党会变成各种利益集团角力的场所——当意识形态认同不再是入党的必要条件之后,党就很容易变成投机者钻营的场所,甚至有演变成被利益集团操纵的工具的危险。
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是垄断集团的形成及其对国家政策的左右。经过19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的改制浪潮,国有企业的数量已经大大下降,剩下没有改的,要么是受到国家产业政策保护的企业,要么是拥有垄断地位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经营者亦官亦商,既得到作为商人的好处,也同时可以用官员的身份影响政府决策,以获得更多的好处。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政策的执行工具的职能在弱化,而它们作为利益实体的角色在强化。
纵使在中央层面政府可以继续保持一个中性的态度,我们也很难保证在地方层面政府不被利益集团所利用。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地方政府与商业精英的结盟越来越深。
在中国,地方政府为争夺投资,竞相对外来资本给出优惠条件,而这些条件往往超出了一个亲商环境的需要,甚至超越法律;另一方面,地方商业精英越来越多地通过人大和政协参与到地方政治决策的过程中。商业精英对地方政治的控制使中国有可能陷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中所经历的境地,即民主经常意味着精英统治。
地方政府也有成为商业实体而非政治实体的倾向。地方政府像企业一样管理日常事务还不是太大的问题——很多发达国家的城市管理是交给私人公司完成的;问题在于,政府制定决策的方式和公司制定决策的方式一样,追求的是单一的目标——经济增长。忽略增长以外的问题使政府更容易采取偏向精英阶层的政策,而忽视大众的意愿。
中国是一个内部差异巨大的大国,在“国党”体制下,要实现对官员的监督非常困难。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会变得不那么迫切,拧在官员们头上的螺丝就要松动,腐败和懈怠就会乘虚而入。
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多元化的阶段,党的意识形态必须能够容纳其它的主张;换言之,它必须是罗尔斯意义上的重叠共识,即所有主张的公约数。这个公约数的边界还可以讨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自由民主必然是它的核心部分,因为只有自由民主,才能保证各种主张的表达。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一夜之间实现全面的民主,同时,我也不认为民主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民主的精髓是在遵循预设的规则和程序条件下达成妥协,其结果当然不可能总是合意的。我所提倡的,是从合法性来源出发,实现国家治理方式的范式转变,即从寻求基于表现的合法性转变为寻求基于表现的合法性和基于程序的合法性的结合,其实质是使民众的参与更加制度化。
从中国目前的情形过渡到全面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近期,实现国家治理方式的范式转变,将有利于我们校正过去三十年单纯强调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为继续保持政府的中性性质创造条件。
首先,它使政府可以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来自于那些没有从片面增长中得利、得利不多或是利益受损的人们。这个人群的数目可能很大,民主要求政府考虑到他们的要求。即使这部分人的数量很少,民主也可以让他们有机会发出声音。公众的参与可以揭示经济增长的隐含成本,它增加了政府在经济增长的不同方式之间进行选择的可利用信息。
第二,更多的公众参与提供了一种打破政府-商业联盟的机制。民众的参与对于监督大型垄断国有企业显得更为重要。发达国家也有成功的国有企业,但这些国有企业是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的。
第三,基于程序的合法性减轻了政府官员对经济增长的责任,让他们不再需要仅仅从经济表现中获得合法性。政府官员争取再次获选的激励促使他们谋求实现选民的全面利益。
些表现指标,其中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一项。这使得政府官员有强大的动机调动他们手中的一切资源来推动更快的增长。“逼民致富”不是一句玩笑,而是很多地方的现实,这些强制性的措施大多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经济活动的多样性消失了。人们拥有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对风险的偏好是不同的,因此要想充分发挥他们在这些要素上的比较优势,多样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强迫人们做同样的事情,“逼民致富”只能让民众变得更穷。
从中国目前的准备来看,从基于表现到基于程序的合法性的转变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激进的一场变革。正在展开的“第三次思想解放”将给中国带来一个发展模式的转变,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转变为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在一个越来越多样化的社会里,如果保证人民权利的基本程序得不到重视,那么社会和谐也就无从谈起。和以前几次一样,这个转变将开创一个新时代;但是,与以往强调经济增长和市场建设的转变不同,这次转变更可能带来政治结构的变革。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电子邮箱yyao@ccer.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