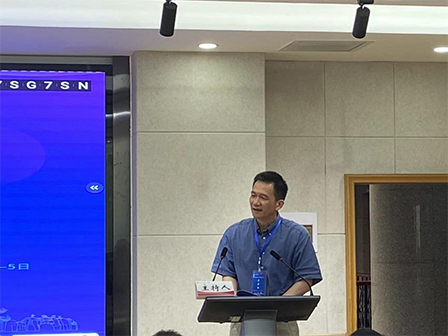改革现行农地制度中的公正问题
观点 · 2008-04-21 00:00
返回上海大学的范剑文给我来信,在指出现行土地政策有很多缺陷,改革呼声很高之后,明确肯定土地私有会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不过,他接着问道:“如果我们认同改革目标是土地私有化的话,问题的关键就转变为如何转型的问题,...
上海大学的范剑文给我来信,在指出现行土地政策有很多缺陷,改革呼声很高之后,明确肯定土地私有会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不过,他接着问道:“如果我们认同改革目标是土地私有化的话,问题的关键就转变为如何转型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目前在此岸,如何过渡到彼岸的问题。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让人满意的转型方案。”
在他看来,“任何一个改革方案的提出必须能够在社会所能接受的‘公平’和‘正义’的前提下才能展开,如果偏离了社会所认同的‘公平’和‘正义’,强制推行,只会产生两个结果:一个是改革夭亡;一个是社会分崩离析,处于崩溃的边缘。”他以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所造成的后果为例,认为改革国企产生种种弊端,在推进和提升企业效率的同时,也造成大批下岗工人和一大批巨富。用他的话来说,“我们的宣传一直说,一个企业的员工都是企业的‘主人翁’,但是眨眼之间,一部分主人翁变成了真正的主人,另一部分主人翁被赶出企业,变成了下岗工人。这样的结果让人们如何接受?”
范剑文的看法有些言重。一般来说,社会没有那么容易崩溃。但是他的看法很有代表性,值得认真回答。在我看来,国有企业对国家财政构成沉重包袱,而且今后只会越背越重,成为我们快步前进的严重障碍。况且顶着“主人翁”的桂冠,不但必须忍受贫困和匮乏,而且子女只能上山下乡,这样的“主人翁”地位又有什么实质意义?所以,快刀斩乱麻,使国企尽快民营化,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由于配套改革没有到位,在操作时确实常常不透明、不公平。范剑文提出,改革土地制度不应回避公平和正义,我认为完全正确。
在自然村或行政村的范围内,按每家在村中的人口比例来平分集体土地的私有化方案,既符合公平和正义的标准,又符合可操作性的原则。而且根据科斯定理,只要允许交换,整体效率也会逐步提高。解散公社时,土地便以平均的原则分给农民。联产承包取得巨大成绩,表明农民接受这种分配原则。我对这种私有化方案不但深表赞成,多年来也如此主张。
然而,范剑文对此深有疑虑。在他看来,“按照属地原则,农民平分本村的集体所有制土地并不可行”,因为“大城市郊区的农民(会)出现大批的千万富翁。人们必然会问,这些人的财富来源是否正当合理?如果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北京、上海郊区的农民身份就导致了他们拥有巨额财富,那么其他地区的农民作何感想?那些辛辛苦苦工作的上班族又会怎么想?这是否又是另外一种二元体制?”
范剑文如此发问,我为他深深惋惜。他显然已把可操作性抛掷脑后,却醉心于绝对平均主义。按照绝对平均主义的逻辑,天下大概没有公平、正义可言。例如,即使国企在改制时对下岗职工的补偿比现在 “公平”、“正义”,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那么农民呢?既然国企是全民所有,农民通过价格的剪刀差对国企的建立和发展贡献巨大,难道他们不应该从国企改革中得到一些补偿吗?再如,1949-1952年的土改也是 “不公平”、“不正义”的,因为当年上海农民分到的是寸金之地,北京农民分到的是风水宝地,自然比甘肃、青海的穷山恶水之间的薄地值钱得多。
进而言之,上海和北京居民的身份和享有的权利不也代表了 “不公平”和“不正义”吗?北京继承八百年古都的种种文化、建筑、政治、经济和历史遗产,上海天然享有优越的江海位置带来的工商繁荣。两地居民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并非完全来自本身的努力,而有天时、地利的很大贡献。这公平吗?难道不应该对他们课以重税,并将税收所得转移给全国老百姓吗?更极端地说,如果用北极圈里的爱斯基摩人的生存环境作为平等的起点,那么地球上大部分地区人类的生存环境对爱斯基摩人来说都是不公平和不正义的。再如,以姚明的身高、刘翔的长腿而允许他们参加比赛,也可以说是对一般凡夫俗子的不公平和不正义。这样的逻辑,恐怕不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问题更加复杂,使人群中的矛盾更加尖锐。
从大跃进到十年文革,我们已经浪费了20年的时间。那时的破除一切所谓 “资产阶级法权”造成的差异、寻找绝对平均主义的道路,结果却导致物资极度匮乏,经济濒于崩溃。这说明,脱离效率去寻找所谓的“公平”和“正义”,必然坠入虚无缥缈,不着边际。所以,追求公平和正义,只能在不牺牲效率的前提下进行,也即,只能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前提下逐渐改进蛋糕的分配。我在上一篇专栏中指出,“如果能够建立不靠世袭,不靠政治垄断,人人有相同的几率在公平竞争的土地市场上获得土地,人人也有相同的几率在这样的土地市场上失去土地,这样一种能够更有效使用中国最稀缺资源的制度安排,有什么不好呢?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可以如此做,为何土地市场就不能如此做呢?”
这就是说,我们要追求的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人们的先天秉赋因人而异,后天努力参差不齐,强使结果平等,反而造成不平等、不正义和贫困的蔓延。只要机会均等,生产要素保持高度流动,好逸恶劳者就会很快丧失财富,而勤劳能干者则能很快获得财富。如此的制度,便会促使人人勤奋向上,并因人人分享到效率提高带来的好处,必然也会容忍结果的不平等。这才是值得向往的公平和正义。土地私有是通向这种机会平等的制度安排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所以,追求公平、正义,只能以承认现存的差异开始,逐步建立机会均等的制度,否则就只能回到暴力革命的怪圈。
况且,我绝不相信,在人口稠密的上海,按农民人头平分土地,大概每人也就一二亩,如何产生“大批千万富翁”?这倒是我要请教范剑文的。在我看来,反倒是在目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由于土地管理权高度集中在村镇干部手中,农民手中并没有法律认可的地契。而村镇干部在高压之下或利诱之前,往往用集体名义签字盖章,向不法官员和开发商非法转让土地获利。例如,最近一期《财经》杂志披露,陈良宇三大罪名之一,就是利用职权,助其弟陈良军非法获得郊区的600亩土地使用权。其弟后来将此一转手,获暴利1.18亿元人民币。折算下来,每亩价格20万元左右。普通农民能不能拿到这样的价格呢?假设能,即使每个农民分到5亩,补偿不过100万元,扣除各种税费,离千万富翁恐怕很远。
土地私有制的优点之一,倒是使凭借行政权力大肆圈地的成本极大上升。在土地私有制下,市场交易只认地契,不认批文。农民拥有获得法庭公证、受法律保护的地契,如果拒绝出让土地,圈地者除非从他们家中搜走地契,否则就无法实现对土地的合法拥有。所以,圈地运动除发生于英国的公地外,便是中国的集体土地。正是土地集体所有制为违法乱纪者侵吞集体土地大开方便之门。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呼吁土地私有,以保护弱势的农民群体的原因。强势群体凭着唬人的权势或高人一筹的智力和体力,越是产权界定不清,越是可以浑水摸鱼,侵吞良民百姓的财产。所以,产权是用来保护千千万万普通百姓、限制有权有势者的巧取豪夺的。
范剑文对上海郊区农民得到的土地补偿费远远高于内地农民,似乎深感不平。如果实行土地私有,上海郊区农民得到的补偿会比现在更高,会使他更为想不通。我想以下的解释也许能使他释然开怀。众所周知,上海地价位于全国前列,是由于全球化后的上海区位优势更为突现,所以工商繁荣,人口密集。上海集聚效应尚未穷尽,从效率角度看,自然还应大大拓展。上海郊区的农民出让土地后,当然希望成为市区居民,因而必然面对全国最贵的房价和最高的物价。如果我们不希望他们在失去土地后,立即成为城市贫民,或不希望因为他们拒绝出让土地,而使上海无法坐收集聚效应带来的效率提高,对他们的补偿自然要反映上海的房价和物价。
因此,只要对农民来说土地是平均分配,并按市场价格补偿,就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也符合效率的原则。同样的理由可以用来解释在城市的拆迁过程中,一些市民为什么会拿到较高的补偿 (我这里假设被补偿者没有违法乱纪、虚报房价),因为他们所放弃的土地使用权因位置原因而能带来效率的提高,因而有极高的市场价格,同时他们搬迁后仍要面对高居全国首位的房价和物价。
范剑文的最后一个疑问是,“这种私有化会否在中国产生一个一无所有的阶层,即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身无一技之长,如何生存的问题。目前的土地制度就算有各种缺陷,它至少保证了8亿农民的基本生活。而私有化之后的土地兼并,必将在中国造就一个赤贫阶层。中国是否为这个阶层的到来做好了准备?目前政府的社保体制还只是在城市范围内展开,农村的社保还仅仅在规划中。如果农村的社保没有准备好就推进改革,结果是不堪设想的。”
其实,对每一项改革开放措施,我们都可以同样质疑。例如,从计划经济改为市场体制,我们可以问,由此而来的激烈竞争,难道不会出现大批破产企业、数百万下岗工人吗?要建立和发展股市,我们可以问,股价的剧烈涨跌难道不会导致大批小股民的投机失败、倾家荡产甚至跳楼自杀吗?推行对外开放,我们也可以问,难道不会出现大批民族企业在外企冲击下无法生存、频频倒闭吗?在没有完整的社保体系情况下,推出这些改革开放措施,我们更可以问,这样做,风险不是太大了吗?
显然,所有这些质疑的答案不问自明。可是我们会就此放弃改革吗?不会。就拿上述最后一个质疑而言,大家认识到,社保体系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东亚经济在起飞期间及其后长期内,也没有完善的福利体系,至今它们的福利还是无法和欧美相比。它们如此做也是基于自身的经济实力,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中国自然无法例外。当然,我和大家一样,希望中国这方面能做得快些、好些。其次,对市场经济,对股市,对开放政策,我们同样不能求全责备。通过经济学理论的论证,我们确信这几项措施的收益远大于范剑文担心的那类代价。而且,如果不改革、不开放,这类代价今后只会越来越大,更难负担。所谓两害相衡取其轻,两利相较取其重,便是经济学教人如何做选择的诀窍。
同理,对土地私有也不应求全责备。认为私有化下的土地兼并必将在中国造就一个赤贫阶层的说法,过于武断了。把土地分给农民,并允许有买卖的权利,其实也是一种能动型的社会保障。自古以来,农民十分懂得年轻时勤俭节约,努力置产置业,以解决晚年的养老。从中国两千多年前实行土地私有以来,以有限耕地而能养活高居世界首位的人口,并且国力和人口持续上升的历史事实看,即使当时非农就业机会极为有限,土地私有下的兼并也没有导致大量人口难以生存的状况。原因是失去土地者不会身无一技之长,他们至少懂得耕田种地,所以依然有做长工和佃农的机会,也有重新拥有土地的希望,其收入也一定足以使他们的大部分人成家立业,繁衍后代,否则中国的人口总量应该是逐渐萎缩的。中国历代统治者不懂利用发展工商吸收剩余人口,这是中国近代衰弱的原因之一,与土地私有无关。
在当代条件下,非农就业机会大量涌现,土地兼并的负面后果更为减轻。如果实行土地私有,愿意继续务农的,不但会百倍珍惜分到的土地,还会通过勤劳节约或金融服务,逐渐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立志进城发展的,土地私有制下的公平补偿会诱使他们更快出售土地,获得启动资本,平滑融入城市,并使留下的农民逐渐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有了土地所有权,农民自古以来拥有的融资权利又可恢复,通过抵押土地或房产获得资金,扩大生产,增加收入。万一失去土地,除继续有做长工和佃农的机会,也有机会通过自身或后代的努力重新拥有土地的希望和权利。既然现在城里人大部分靠打工谋生,自然没有理由取缔农村的长工和佃农。这样的解释,能否使范剑文以及有类似想法的读者朋友重新思考对土地私有的疑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