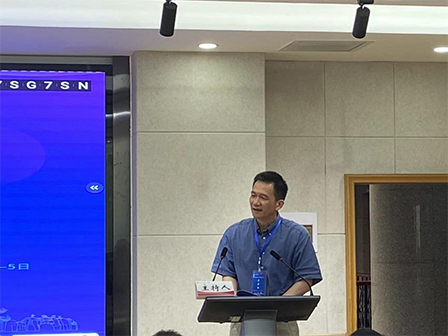王勇:内生宏观经济政策、技术引进与经济发展(之一)
观点 · 2007-10-05 00:00
返回内生宏观经济政策、技术引进与经济发展(之一) ——基于新近经济学研究的一些理论思考 王勇 [1]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候选人) 2007年9月初稿,欢迎评论意见! (《浙江社会科学》约稿) 【韦森按】自1998年我从澳洲回国执教以来,...
内生宏观经济政策、技术引进与经济发展(之一)
——基于新近经济学研究的一些理论思考
王勇 [1]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候选人)
2007年9月初稿,欢迎评论意见!
(《浙江社会科学》约稿)
【韦森按】自1998年我从澳洲回国执教以来,目前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做博士候选人的王勇是我最值得骄傲和常常向其他学生和朋友提起的一位学生,以致于我经常说王勇是我一生教过的学生中的第一人。王勇原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96级的学生。1998年我回国第一次走向国内大学讲堂,就发现王勇是复旦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从复旦毕业后,王勇免试直升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攻读经济学硕士,在林毅夫和宋国清二位兄台的直接教带下,在北大加深了他的现代经济学和数学的理论功底。从CCER毕业后,王勇又立即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这样世界的经济学重镇深造,师从卢卡斯夫妇。对于自己最骄傲的学生之一,作为老师的,也许不宜在别人面前过多褒扬。我这里只想说明一点,这多年来,我和王勇不仅仅保持了一般的师生关系,也是能相互推心置腹交谈的朋友。毅夫兄常常说,20世纪末和21世纪中国经济的伟大复兴,将会为未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供了一个合宜的环境和土壤。我深知毅夫兄的这句话的深意,这是他深怀着对未来中国青年一代经济学人的嘱托和期盼而说的。就此而论,尽管在对中国经济学的整体现状的估计上我没有毅夫兄那样样乐观,但这一点上,却与毅夫兄有着同样的期盼!
2007年9月9日韦森谨识于复旦
本文试图通过对近十年来相关经济学文献的选择性回顾和简单梳理,重点结合笔者本人的一些探索性观察与研究,对于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内生性宏观经济政策和技术引进问题作一个非技术性的介绍和讨论。这是宏观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中一个极为重要、复杂、庞大、却又令人激动的比较新的研究课题,它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其他学科也密切相关、日益交融。为避免我们的讨论失于宽泛或者过于“形而上”,本文将以一个具体的与中国有关的宏观经济现象为主线来引导我们的经济学分析与方法论阐释。
一、问题的引出
众所周知,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世界上最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之一就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崛起。“龙象之争”受到了国际学术界,工商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2]。亚洲的这两个国家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国而印度则是在1947年独立。两国在50年代到70年代都有很明显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经济的特征。两国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市场化经济改革,随之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速度都超过8%,远远超过了世界平均速度2%。尽管如此,中印仍然都属于“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的人口都超过10亿,共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两国的人均GDP在2005年仍然都排在全世界的100名之外。
但有趣的是,这两个具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国家在吸收对外直接投资(FDI)这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上却存在着巨大差异。30年前两国的FDI都几乎为零,然而,在2005年,中国大陆吸收的FDI流量将近720亿美元,竟是印度的12倍![3]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么大的差距?
首先我们需要分析影响FDI吸收量的决定性因素有哪些。从要素价格来讲,虽然中国吸引的外资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做出口加工贸易。可是作为人口大国的印度,劳动力平均成本比中国还要便宜,2005年印度的人均GDP为680美元,不到是中国的一半。从政治制度上来说,印度是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而中国宪法则明确规定中国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语言上来说,印度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英语的普及和使用要先于高于中国。这些在理论上都应该更加有利于印度吸收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FDI。可为什么事实会恰恰相反呢?
显然,两国经济基本特征的差异和粗线条的政治制度比较都无法令人满意地回答这一问题。然而我们观察到:在中国,各地政府党政一把手都非常积极地直接参与吸收外资的谈判,各地政府不但在市政硬件设施建设上都作了巨大投资,而且争相为境外投资者提供税收和土地征用等方面各种优惠条件,这些都远远优越于国内企业所享受的待遇,以致于产生了资本绕道回流(round-tripping)的现象,即有些大陆的资本以各种隐蔽的方式绕过资本项目管制先流入香港等地,然后假借外资名义回国套利[4]。 而在印度,在80年代的经济改革主要是为了增强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取消了很多经济管制,但是限制外国企业的进入。直到90年代初的国际收支危机才触发了真正市场化的对外开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各邦政府之间对外资的争夺也远远不如中国竞争的那么激烈,一个间接的可观察的证据就是印度各地的道路交通等市政建设,相对于中国而言显得非常落后。这些经验事实提示我们,中印两国FDI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两国政府对于FDI的欢迎程度和政策优惠不同。但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政策会不同?这就涉及到所谓的内生性经济政策问题。
二、内生经济政策
在经济学中,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主要是规范性的(normative), 即给定一个外生的经济政策,经济学家们构建一个高度抽象和简化的理论模型作为思想实验室,分析这个政策所产生的客观的福利后果。然后对不同经济政策的福利后果依照某种标准进行比较,最后给出“最优政策”的建议。然而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宏观经济学家开始进行实证性的(positive)的政策分析,即在现实中不同的经济政策究竟是如何产生和变化的,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经济政策的制定,修改,推行这一整套政治过程,涉及到政治与经济制度,涉及到各社会阶层中不同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这种研究与现实的距离无疑更加贴近了,但分析难度也大大地提高了。
为什么宏观经济学家们开始对经济政策的政治过程会如此感兴趣呢?从研究内容来看,笔者认为,这至少与以下五个经济学中著名的“尴尬”或者“谜题”有着密切的关系。
(1)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同意自由贸易是最有经济效率的,但是国际贸易却一直不是自由的。所有国家仍然对本国企业采取不同程度的保护主义政策,至今各国之间仍然在进行着艰难的多边谈判。即便在非常崇尚经济自由的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经济学家曼昆教授就是因为坚持推行自由贸易而遇到很多政治压力,只好提前从华盛顿卸任。这些都促使国际经济学家们不得不认真地去考察现实世界中与贸易政策相关的政治过程[5]。
(2) 对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经济理论家们曾形成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一致认为转型应该一步到位。但是奉行这种“休克疗法”的前苏联曾发生持续的严重的产量下降,大量失业,和社会动荡。而奉行渐进改革策略的中国却稳步地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基本稳定。这促使制度与发展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开始重视经济政策变革的经济与政治的可行性问题[6]。
(3) 经济学家们发现,世界各国的经济绩效之所以存在巨大差异,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可是为什么很多落后国家就是不引进和吸收现有的更加先进的生产技术呢?这促使宏观与发展经济学家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究竟是什么经济与政治力量阻碍了很多穷国对先进技术的引进[7]。
(4) 跨国比较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不同的发达民主国家在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以及政府开支占总GDP比例上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研究发现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及政府的财政政策都与选举制度系统相关,比如议会制国家平均要比总统制国家有着更激进的再分配政策和更高的政府开支比重。 这些促使宏观与公共经济学家们去系统地考察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等政治制度细节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8]。
(5)新制度主义代表性人物诺斯认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积累,技术的进步,这些其实是经济增长的本身而不是增长的根本原因,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效率。那么为什么很多落后国家的非效率的制度能够长期延存?制度惯性与动态的微观机制是什么?法律作为社会契约究竟如何影响制度效率?民主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促使制度与宏观经济学家,包括演进博弈论者,都不得不审视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的经济与政治利益集团对于政策与制度的不同偏好与需求,探求社会的法律起源,以及其它因素对制度动态的影响[9]。
从分析方法上来看,在经济政策与制度形成的政治过程中几乎不存在一个显性的市场价格来引导政治力量与资源的均衡配置,相反地,这个过程几乎总是各利益集团之间的一种策略性的互动过程。这就使得博弈论在内生经济政策与政治过程分析中显得大有用武之地。因此很多博弈论学者近年来纷纷转入研究与政治过程中的投票,选举,政党,民主等问题。当然,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如今博弈论在产业组织与公司治理等领域的应用已经非常成熟,要做出大的新的突破可能会更加难了。
内生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也许联系宏观经济学的整体发展图景来看会更加清楚。 我们知道,基于完全信息下的动态一般均衡宏观理论,作为当代宏观经济学的基准范式已经日趋成熟,其实质是假定了一个以市场竞争与交易为核心特征的制度结构,在给定偏好、禀赋、技术假设下,市场制度以均衡价格的形式来协调各优化主体之间的选择以满足相容性的资源约束。但是当我们分析很多具体的宏观经济现象时,特别当涉及到不完全信息、不完备市场、激励等问题时,我们就必须在理论模型中将这些新的制度特征与信息结构做得更加丰满。事实上,我们的确看到近二十年来的宏观理论中,国内与国际金融中介市场(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以及政府国际债务问题 (sovereign debt),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税收问题,动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风险分担(risk sharing)和失业保险设计问题,非共同知识(uncommon knowledge)条件下的各分散经济主体之间的投资、汇率攻击等协同问题(coordination game), 以及理性的“羊群行为”(herding behavior) 等等,都开始考察非价格协调下的博弈均衡行为。在这一趋势下,对内生经济政策与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数理建模也就显得不那么突兀了。特别是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经常是缺失的,而作为规则制定者、修改者、与执行者的政府在经济体中还经常充当直接的参与者,因而价格信号经常是失真的,导致各优化主体不得不基于其它非市场价格的信号来决定经济行为,因此我们经常无法完全撇开政府而以标准的市场一般均衡框架来探讨发展问题。
制度政策分析与市场行为分析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科斯定理的适用性。科斯定理指的是,只要产权界定清楚,市场完备,那么经济资源的配置就一定能实现帕雷托效率,而与产权如何配置无关。然而,在政治过程中,政治权利的清晰界定却并不能保证一定能够达到具有经济效率的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另外,法律上的(de jure)政治权利与实际的(de facto)政治权利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政治地位低下的社会阶层有可能通过暴动或者政变来获取更多的政治权利。这种潜在的对政治权力与结构进行再分配的能力,尽管没有制度保障和法律的明确承认,却也会对经济政策形成的政治过程产生重要影响。
三、地方政府竞争与实际产权保护
现在让我们回到中国的例子。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之所以这么积极地争取外资,一个最为直接的解释可能就是外资的吸收量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考核指标?换个角度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形成有效的政治联盟对政府施加足够大的影响以抵抗外资进占中国市场?从外资的供给方面来看,为什么境外投资者相信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各级政府会从法律上严格保护而不是没收和国有化他们的产权?这些都很难讲是纯粹的经济学问题,但的的确确是经济学家们为理解现实经济现象而绕不过去的问题[10]。
从近年来中国的外资来源构成来看,美欧国家和日本等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其中有很多主要瞄准了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比如房地产、汽车、与信息电子产品消费。在这些行业中外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内企业形成了争夺市场的竞争性的替代关系。这些国内企业,包括很多国有企业,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润,自然有激励动用一切经济与政治资源去游说中央政府通过制定关税和企业各税率等各种措施来遏制外来投资者的竞争。
另一方面,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而言,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是极为重要的政绩考核标准,这是因为中国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形成了实质上的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钱颖一和Roland (1998)分析了这种财政联邦主义对国有企业 “预算软约束”问题的克制作用。Shleifer 和 Blanchard (2002)则指出中国比俄国的财政联邦主义远为成功,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有一个更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协调各地方政府的行为,而这一点也保证了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的可操作性和效率(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 1992)。为便于分析,让我们先忽略地方间的转移支付,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该地的国内企业的税收和外资企业税收,这些税收收入按照事前法定的比例与中央政府分享。因此,如果国内企业,尤其是很多国有企业,因各种原因总体经济效益不好,那么外资企业就更会受到地方政府的扶持与青睐,但是地方政府又有哪些政策变量可以使用呢?面对强大的中央政府调控,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法律上没有太多的政策自由度,比如无法像美国州政府那样可以通过立法来直接改变税率以争取FDI,但是地方政府还是有很多隐性的途径来影响外来投资者的商业利益,比如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对土地转让的控制权、各种商业承包的拍卖权、卫生质量检测、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公共品提供、涉及外资企业的司法裁定与执行、有关商业行政管理的手续、国有金融机构的服务等等对外资企业进行歧视,以增加其商业成本。我们把这些笼统地归纳为影响外资企业的实际的(de facto)产权保护成本,因为这些是外资企业为了维持正常的商业运作,而不得不支付的,但本不应当承担的制度成本。这自然是与目前中国的法制尚不健全,相关制度供给不足或者不配套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也为官员个人的寻租行为提供了制度土壤。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进行同指标的量化考评(yardstick competition),而且具有绝对的人事任免权,因此如果政治激励与经济激励同时促使各地政府对于外资进行激烈争夺,那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遏制官员的机会主义行为,竞争性地降低外资企业的实际产权保护成本,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制度补漏过程,优化了的相关政策的经济效率[11]。
作为潜在的境外投资者,它可以选择通过出口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也可以选择绕过贸易壁垒到中国直接投资,当然也可以选择既不出口也不投资,这取决于利润的比较。如果进口关税越高、外资企业的利润税越低、实际产权保护成本越低、中国劳动力成本越低、那么投资者就更愿意进行直接投资。反之,则更愿意通过出口而不是直接投资来进占中国市场。作为国内的普通的居民户,他们一方面作为劳动力供给者在竞争性市场上工作赚钱(有一部分居民还拥有国内企业的产权,因此他们的收入中还包括企业的利润分红)。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自然希望低物价(从而低关税)和消费品多样化,他们在垄断性竞争的产品市场上购买各种国内外的消费品。
作为中央政府,它不仅关心来自企业税收和关税的财政收入,也关心全体国民的平均福利水平,同时它也受到来自国内各利益集团的游说与压力,中央政府必须在这些目标之间做出权衡,制订相应的关税税率与企业税率。给定关税水平,如果所制定的外资企业税率相对于国内企业税率过高的话,一方面会提高地方政府对FDI的需求从而诱使地方政府降低其实际的产权保护成本,但另一方面却会降低潜在投资者的FDI供给;相反,如果外资企业税率相对过低,那么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主要依靠国内企业,而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又是竞争性的,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对FDI的需求下降,从而诱使其提高实际的产权保护成本以达到遏制外商进入的目的,尽管低税率有利于提高潜在投资者的FDI供给。因此,税率过高或者过低都会使均衡FDI为零。最后均衡的实际产权保护成本和FDI水平取决于那些内生于各政治经济力量博弈的关税税率和企业税率。如果国内企业利益集团足够强,或者平均国民福利在实际的中央政府目标中不够重要,或者中央政府足够弱(体现在与地方政府的企业税收分成比例足够低),那么就会使得政治过程中所决定的外资企业税率过高,而且关税也高,FDI供给为零。反之则反是。
可见,关于FDI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要涉及到多级政府,境外潜在投资者,国内居民,国内企业主集团等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交互行为,既有市场价格的指导配置作用,也有影响经济政策的政府博弈行为。实际上,上述讨论正是对笔者(Wang, 2007a)数学模型主体部分的语言复述。在那里,我们构造了一个具有单个中央政府和两个对称的省政府的经济模型,严格定义了这样一个同时满足市场出清和纳什均衡的政治均衡,并且证明了这个均衡的存在性。我们还证明,这样的均衡以概率为1的可能性(generically)只出现两种极端情况:要么实际产权保护成本很低(即政府对FDI持非常欢迎的态度)而吸收的FDI总量很高;要么实际产权保护成本很高(即政府对FDI持非常抵制的态度)而吸收的FDI总量为零。我们希望这个模型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在很多正式制度缺位的条件下,政治竞争仍然可能导致政府对于外资的产权进行实际有效的公共保护并且能够吸引大量FDI[12]。这种均衡的分岔(bifurcation) 也许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具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发展中国家,像中国和印度,会有这么截然不同的FDI水平。
本文之所以选取发展中国家的FDI作为例子,是因为它不仅仅是资本流入问题,更是生产与管理技术的引进问题,这些都是宏观发展经济学中与政治经济制度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事实上,Borensztein, De Gregorio, and Lee(1998) 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FDI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资本的投资率的提高。对于中国来说,总的FDI在固定资本投资所占的比例也只有10%左右。
--------------------------------------------------------------------------------
[1]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候选人。通讯地址: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IL 60637, USA. 电话: 1-773-401-0382. 个人主页:home.uchicago.edu/~wangyong Email Address: wangyong@uchicago.edu
[2] 对于中印两国1994年以后的宏观增长比较分析,可参见Bosworth and Collins( 2007)。
[3] 印度FDI的统计方法与国际通用的IMF方法不太一致,有低估的倾向,但是即便经过调整以后,印度的FDI仍然大大地少于中国。
[4] 对于资本绕道回流问题的讨论,还可以参见Huang(2003)。
[5] 关于这方面的精彩综述与详细介绍,可参见Grossman and Helpman(2002)和Dixit(1996)。
[6] 这方面的具体讨论可参见Roland(2000); Lin (2007); Qian(2003); 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1992), Sachs, Warner, Aslund, and Fischer(1995 ), 等。
[7] 可参见Hall and Jones(1999); Parente and Prescott( 2000) ; Krussell and Rios-Rull(1996); Acemoglu, et al (2005, 2007) , 等。
[8] 这方面的精彩论述包括Persson and Tabellini(2001, 2003); Alesina and Rodrik, 1994; Benabou, 1996; Myerson(1997), Alesina and Glaeser, 2004) , 等。
[9] 可参见Acemoglu, et al (2006, 2007); Glaeser and Shleifer, et al (2003); Barro(1996); Knack and Keefer(1995); 培顿·扬(2004), 等。
[10] 其他社会学科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曾有不少的批评。但在笔者看来,很多情况下经济学家是不知不觉地被所研究的经济问题和好奇心“诱拐”到其他学科范畴的,“帝国主义者”有时真的也很无奈!
[11] 与苏联那种以部门为单位的U型政治管理构架相比, 中国的以地方为单位的M型政治管理构架要比前更有利于促进有效的政治竞争与考核,而且还有利于推行地方性的政策试验,使渐进式改革也更为可行。见Maskin, Qian, Xu(2002), etc.
[12] 当然,投资者也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产业组织方式,比如与国内企业合资等等,来规避政治风险,降低实际的产权的私人保护成本。最近的文献主要是集中在不完全契约理论框架下的讨论。限于篇幅,我们不做深入讨论。
来源: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30&ID=389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