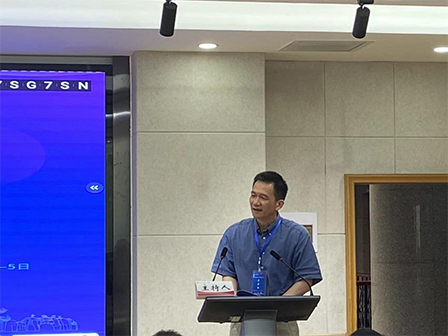“公用品”的消费与生产
观点 · 2007-09-17 00:00
返回政府把公共卫生责任承担起来,有余力再谈其他,这是宿迁医改有普遍意义的第一点。进一步的问题是,公共卫生范畴内的事务,是不是一切由政府亲力亲为?宿迁的答案是,政府负起公共卫生的责任,筹措所需经费,完成防保网络的布局,...
政府把公共卫生责任承担起来,有余力再谈其他,这是宿迁医改有普遍意义的第一点。进一步的问题是,公共卫生范畴内的事务,是不是一切由政府亲力亲为?宿迁的答案是,政府负起公共卫生的责任,筹措所需经费,完成防保网络的布局,同时也可以把部分公共卫生的服务工作,交给私人和民间机构承担。这点重要,也有普遍意义,值得专门讨论一次。
访问中印象最深的,是宿迁把政府直接负责的公共卫生服务网络,扩大到了村庄一级。前文介绍过,宿迁医改的一项发明,是“医防分策”——就是把一般医疗服务与防疫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区别开来处理,前者交给民营医院和乡村私人医生,由政府监管,后者由政府自己打理。具体做法,就是在每个乡镇分设医院和卫生院,前者民营行医,后者“官办”专司公共卫生。这里“官办”的乡镇卫生院,全部由财政投资,全额由政府预算运营,再不是那种政府只抓权、不出粮的名不符合实的“公立医院”了。
但是,公共卫生网络就算建到了乡镇,也还不等于“到底”——农村的基本社会单元是村,绝大多数农民居住在村里。要是乡镇公共卫生机构不能把服务延伸到村一级,“以防为主”还不是一句空话?一旦发生突发性的流行疾病,卫生防保网还有很大的漏洞。可是,从乡镇扩展到村庄,又谈何容易!
宿迁找到的办法很实际,就是政府在乡镇卫生院的预算中,编列了外聘村庄防保人员的项目,要求每个村至少聘任一位村医,用财政经费完成最必要的村庄卫生防保工作。实话实说,开始听市、县卫生局长介绍这条经验的时候,我将信将疑。村庄一级的问题,自己多年来也算做过一点功课,没有那么容易就到底的。后来在沂涛镇卫生院当面细问院长,信有其事。还专门到宿迁籍同学的家乡,在邻近两个村子里找到三位村医,详谈一晚,才算心中有数。
他们划分得很清楚:公共卫生的责任是政府的,所以经费由政府出,公开招聘由镇卫生院主持,工作也由乡镇卫生院指挥、督导;但在到村庄一级具体完成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却是乡村私人医生。这些村医,要竞聘村庄防保员职位,被聘上的就负责流行病、传染病病例报告、0-7岁孩子打防疫针、村小卖店和餐饮的卫生监管、村庄水源水质检查,还要协助农居改厕工作、监管村庄公共场所的卫生等具体工作。
完成所有这些“琐事”,报酬每年2000元。我问村医,你们愿意被聘吗?答,争还争不来。因为村医本来就是亦医亦农,多一点专业工作就多一点收入。除了货币收入以外,当上防保员还意味本领高一些,增加了他们在村民中的号召力,也增加了在农村行医的竞争力。
这就是国际流行的 “公私合作”理念(PublicPrivatePartner,简称PPP是也)的一个体现了。为什么PPP?无非为了更好地动员社会资源罢了。讲过了,公共卫生的责任由政府负责,首先是因为这里存在很多足以威胁他人健康、生命、财产的“致命外部性”,没有政府强制力,办不了也办不好。其次,搞公共卫生,网络化防御和早发现、早治疗,社会成本最低,政府负责的优势比较明显。
但是,政府负责不一定全部由政府包办。政府负责的事务究竟采用什么形式来完成,要不要与私人和民间机构合作,以及用什么样的合作方式,都是可以细加选择的。道理不复杂,因为以不同的方式履行非政府承担不可的责任,组织成本可能不同,工作效果也可能不同。正是为了政府更好地担负非政府莫属的公共职能,才需要在多种模式里选择。
在经济学思维上,要达到问题的这个层面,“外部性”概念看来不中用。不是说世界上没有外部性这回事,而是人群中的个人行为,多多少少总对他人发生影响。不分轻重,凡影响了他人就是“外部性”;也不分青红皂白,凡“外部性”就一定要大动干戈,人类组成社会的代价岂不是太高了?至于任何外部性都要政府出场,政府哪里又忙得过来?刚刚谢世的男高音歌手帕瓦罗蒂,据说早年听邻家婴儿久哭而声音依然洪亮,启发他改进了发声方法。歌王后来举世知名,是要回头感谢邻家孩儿的哭声,还是要求意大利政府抽取 “啼哭纷扰税”呢?
是的,同一个“外部影响”,效果可能正负相间,非要一手抽税一手补偿,忙个不停吗?更重要的是,数之不尽的“外部影响”不理也罢,因为理会的代价大过了收益,还是将就为上。另外一些外部性,由当事人自己讲价钱解决就好,无须他人干涉的。但是有的“外部性”,比如上文不得已造出来的“致命的外部性”,政府不处理就天下大乱。一个“外部性”有那么多不同的含义,用来解释人的行为逻辑不免歧义四起。
我以为比较可取的概念,是“公用品”。可惜这个publicgoods,一开始就被误译为 “公共物品”,甚至“公共财货”。在高举主义之争的地方,学子的注意力难免被引向十万八千里以外,先入为主,以为“公用品”就是“公有的财产”,或者“应该是公有财产”云云,把问题的重点完全歪曲了。
1980年代中读到《卖桔者言》,才知道其中的误差太大。当年五常先生以中文下笔,介绍科斯1974年写下的“经济学中的灯塔”。说的是大海航行,来往船只看不见水下的礁石和其他危险,需要灯塔指示安全的航道。可是灯塔提供的服务,你用也不影响别人也用——甲船看到灯塔的光芒,绕路而行;乙船、丙船来到,照样见灯光就可绕路而行。此“你用不影响他人用”——后来有的经济学书本上讲的“消费不排他”——就是“公用品”的本来意思了。
在行为分析上,“公用品”引出两个推理。其一是英国历史上创立福利经济学的那几位,最有名的要数剑桥大学的庇古教授,断定私人不会投资公用品,因为私人不能强制每个享受公用品的顾客付费,投资没有足够的回报,做不来的。例证就是灯塔,很多船只可以搭便车“偷看”灯塔之光,享受了服务却不对灯塔的建设和营运付费。其二是当代鼎鼎大名的经济学教授萨缪尔逊,他论证,既然公用品多一个人享用也并不增加服务的边际成本,非要每个享用者付费,岂不带来社会损失?两大推论都说非政府出场不可,区别是一路认为政府办灯塔才可强制收费,另外一路认为政府以税收修灯塔,然后“免费”供社会享受,是最优的制度。
轮到科斯出场,只问了一个简单问题 (“英国历史上的灯塔究竟是怎样修起来的”),就让两大派经济名家尴尬不已。原来最早的英国灯塔,收费由皇家授权的船主协会负责,而修建及营运却是私人公司根据与船主协会的合约来提供的!五常的评语我现在还记在心里:籍籍无名的后起之秀,只要一个下过功夫的实例在手,“盲拳可以打倒老师傅”。
是的,在经验科学里,所有理论推断的惟一命运就是接受事实的检验。大名家说公用品非政府不可,逻辑上没有破绽,但怎么解释英国历史上实际上由私人投资建设了多个灯塔的事实呢?后来我把科斯的原文找来细读,发现名山中有更大的宝藏。在那篇妙文快要结束的地方,科斯有一句话让我想了很久,“这种政府筹资的制度不一定要排除私人企业建造和管理灯塔”——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含义呢?
多年后我才得出自己的答案。原来从生产的角度看,世界上本没有“公用品”这回事。还以灯塔为例,从消费方面看,确有“你看不影响他人看”的属性,所以灯塔是公用品。但是建造灯塔和营运灯塔所要耗费的资源,却没有一样是“不排他的”——给定财富和收入,多建灯塔,势必要少生产其他。这样看,是资源在生产方面的竞争性和使用的排他性,才逼得人们把“公用品”的“政府筹资”与“政府建造、政府营运”分开来处理。
经验上,今天的中国也开始把部分国防产品通过国家订货的合约方式交付民营企业生产。国防产品当然是公用品,不过也是从消费角度定义的。从生产的角度来看,要提供国防公用品,资源照样稀缺,因此照样也可以借助市场竞争的压力,动员私人企业参与国防品的生产。在基础设施方面,政府授权私人修建并营运、到期由政府回收的BOT模式,不也是早就见怪不怪了吗?到了公共卫生领域,在政府负财务责任和行政责任的前提下,通过购买私人和民间的服务来扩大有效供给,难道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