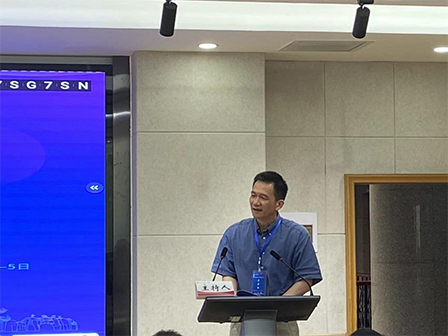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自由、知情权和公共话》
书刊 · 2017-03-07 00:00
返回自由、知情权和公共话语 ——透明化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 斯蒂格利茨 著[1]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宋华琳 译[2] 目 次 一、...
自由、知情权和公共话语
——透明化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

斯蒂格利茨 著[1]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宋华琳 译[2]
目 次
一、导言
二、公共政策中围绕保守秘密和透明化展开的争论
三、公开制度的基本理念
四、保守信息秘密的诱因
五、信息保密带来的消极后果
六、信息保密的实施
七、信息公开的例外
八、信息公开制度的实施
九、结语
译者注:本文是时任世界银行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9年1月27日在英国牛津大学作的报告全文。全文共分九个部分,本文主要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运用了委托-代理模型、信息不对称、寻租等信息经济学理论模型,对政府信息公开透明行政的理念,信息保密的缘起、危害和实践,如何处理信息保密和公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阐述。同时作者从制度层面,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并结合自己在经济领域和经济生活中的阅历见闻,从实证角度做出了精当的分析。本文对于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与实践,都有许多启示作用。
一、导言
言论自由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言论自由不仅是政府不可剥夺的公众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是实现其它基本权利的手段。通过言论自由可以对政府进行必要的控制:新闻自由不仅可以尽可能的减少政府权力的滥用,还可以促使政府更好的满足公众的基本诉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阿马蒂亚·森有力的证明了,饥荒不可能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度出现。[3]因为并非食物总体上的缺乏导致了饥荒,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贫穷地区的穷人缺少获得食物的途径。而言论自由可以将这些问题曝光,问题一旦曝光,舆论和公众都无法再容忍政府对这些问题无动于衷。
我进一步要论述的是,在民主社会里,知情权是一项基本权利,公众应当知晓政府在作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作。更为直白的说,我认为这里隐含着一个假定,那就是政府行为必须透明公开。在过去七十年里,一味强调保密带给我们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在许多国家秘密警察都在最无情的践踏着公众的基本权利。当然直到今天,类似的保密观念和行为还在许多所谓的民主国家普遍存在。我们应当明了,这样的保密背后蕴藏的是行将终结的全能主义政府理念。这样的保密观念不仅与民主价值背道而驰,也损害了民主过程;这样的保密观念的前提预设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彼此的不信任,同时又进一步加剧了彼此的不信任。
弗朗西斯·培根曾经指出“知识就是权力”(Knowledge is power),保密则使得政府可以通过对特定领域知识的排他性占有,来扩张自己的实际权力,使得即使是言论自由也很难对政府权力加以有效控制。简而言之,言论自由对于民主社会的有效运作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没有信息获得权利,它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法体现其核心价值和功用。
保守秘密也许会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举个例子说明,就拿我们半个多世纪来若隐若现的美苏争霸来讲,美国参议员Moynithan在他1998年的新著《保密:美国的体验》一书中,有力的说明了冷战以及相应的美苏军备竞赛等活动,都受到了双方军备设施信息的保密的影响。[4]通过今天更为透明公开的信息,我们可以发现,前苏联并不象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描述的那样,它并非我们想象中的工业上的巨人,军事上强大的对手。
在今天的讲座里,我将对政府如何进一步实现公开化透明化加以着力论述。作为一个美国人在英国作这样一个讲座,这似乎多少有点滑稽,因为美利坚合众国和大不列颠王国是全球政府公开程度最高的两个国家,他们为其它许多国家树立了榜样。但在此我依然要指出:即使是英美两国政府,依然保守了太多不应保守的秘密,太多需要公开的内容依然没有公开。只有直面并解决我们公开化透明化进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全球其它国家的样板和楷模。
二、公共政策中围绕保守秘密和透明化展开的争论
在对我论述的主题,保守秘密的起因和后果之前,我想首先谈一些私人化的感受。我对于信息公开问题的关注和兴趣可以说由来已久。和我的同龄人相似,是在越南战争期间,形成了我对许多社会基本问题的看法。60年代我和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的其它同仁一起讨论的那些场景,至今还栩栩如生的浮现在我的面前。当时这个顾问委员会的职能之一就是为总统提供经济预测,对于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而言,我们都知道政府在越战中的投入比它宣称的要大的多,但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政府在越战问题究竟投入多大,我们甚至都不知道究竟是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作为约翰逊总统的经济顾问的真正职责和职权范围。也许许多人都可以回想起,当时约翰逊总统在极力寻求“大炮与黄油”(gun vs. butter)之间的平衡,他希望自己在反贫穷战场和越南战场两个战场上都取得胜利,他试图通过保守信息秘密来欺骗愚弄人民,而招致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通货膨胀,在后续的十年里,又因为石油危机等问题加剧了经济局势的动荡不安。当时我们这些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年轻助教都在讨论这样一些问题,总统经济顾问的职责是什么;他们对具体态势的信息应该了解到什么程度;如果政府不肯提交真实的经济预测,这些经济顾问是否应该辞职;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在类似的态势下应该做什么。三十年后,当我出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之际,我发现依然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也令我追忆起三十年前的情境。
几年后,当我出任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时,我参与了英国政府的部分决策咨询工作。但我被要求在《公务员保密法案》( Official Secrets Act)上签名,保证自己保守相关秘密。这让我感到十分困惑,英国并不在战争状态,我做的一切都和国家安全事务相距十万八千里。这样的保密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理念呢?当然对我而言,这样的保密签名主要是一个形式化的手续,但正是这样一个形式化的手续,引发了我对此浓厚的兴趣和思考,今天正好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我愿意在牛津大学,从更开阔的视角对政府公开问题加以审视。
作为一名公共部门经济学家,长期以来我一直在阐述和论证透明化公开化的价值。在我早期完成的一本教科书中。我通过对两种赋税制度的比较,说明了一种好的税制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透明性,而我对公司税的主要批评之一就在于其税制不够透明。
后来在美国出现储蓄和信贷危机之后,我的研究兴趣逐渐转移到金融经济学领域,我也成为倡导鼓吹更为透明化会计制度的积极分子。我赞成调至市价(mark-to-market)的会计制度,也就是说让银行按照市价记录所有的资产。[5]我也指出了实践中对资产价值价格的严重扭曲。但是,对于那些不投入市场的资产如何记价呢,对于这样的不同资产如何比较并区别对待?这背后隐含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更为有效更为准确的利用我们需要的信息,但是我们如何度量不同的会计制度,说一种制度比另外一种制度更精确?在风险投资领域也依然出现类似的问题,难点就在于如何度量长期借贷的风险,市场价值变化的风险与什么因素相关,面对多变的市场,我们很难说哪一笔长期信贷业务是绝对安全没有风险的。
以上在公共财政学和货币银行学两个领域的有关问题,都说明了透明化在公共领域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在过去三十年里,我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投入了所谓“信息经济学”(economics of information)的研究,研究信息不完全的后果,对信息收集和信息隐藏的激励与约束。似乎是自然而然的,随着透明化公开化日渐成为公众的热门话题,“信息”也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而我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阐述信息在公共决策中的意义与作用。
三、公开制度的基本理念
到这里我才进入本次报告的主题,我将从七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将讨论公开制度的基本理念;第二部分中,将探讨政府保密的激励动因;第三部分我将追溯政府官员一味保密带来的负面影响;第四部分中,我将评述政府在实践中是如何保守秘密的;第五部分中,我将讨论免于信息公开制度的例外条件和情况;第六部分中,我将讨论在公共领域扩大信息公开力度所需要的一些基本要素;在最后,我将试图对以上内容加以整合,提出对于民主社会下的公开化进程提出个人的意见与建议。
也许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长久以来,公众就对政府在公共事务领域的保密问题给予了关注。[6]最早的对信息保密的抗议呼声是对新闻审查制度的抗议,这同言论自由的主张相伴相生的。[7]约翰·密尔顿在1644年完成的名著《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一书中,记述了相关经典案例;而詹姆斯·麦迪逊,作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设计师,在修正案中为公众的言论自由权利提供了宪法保障,他的以下论述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所在:
公众要想成为自己的主人,就必须用习得的知识中隐含的权力来武装自己;政府如果不能为公众提供充分的信息,或者公众缺乏畅通的信息渠道,那么所谓的面向公众的政府,也就沦为一场滑稽剧或悲剧或悲喜剧的序幕。[8]
功利主义法学家吉米·边沁基于“由最广泛的公共性来矫正的个人利益”观念设计了他心目中的宪制制度,将公共性作为遏制暴政的首要控制手段。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他的名著《自由论》(On Liberty)中,指出无论在任何条件下公众的审查都是有益的,它是甄别是非善恶的最好途径。[9]在密尔的《代议制政府》一书中,他进一步陈述了“公共性和讨论的自由”(publicity and liberty of discussion)的观点,并强调了公众普遍参与的价值。[10]
Walter Bagehot在出任《经济学家》刊物编辑期间,发展并整合了他的“讨论的政府”(Government by discussion)的观念。现代信息经济学强调知识一旦公布于众,并变成公共产品无法再将其私有化。而Bagehot也以其独特的进路阐释了类似的观点,论述了信息在自由选择中的重要作用,他写到:
今天认为民主好似墓穴,它带走了归人,却并不带来什么。而这也同样适用于“讨论”。当你提交了你的观点供神明裁判之后,你再也无法将其收回;你无法将其讨论事项再披上神秘的面纱,也无法再用神明的名义将其遮掩。它让我们更为公开的自由选择,将亵渎神明的窃议曝光公诸于世。[11]
在我看来,上述论述中以麦迪逊等的正面论述最为有力:民主过程中的实质性参与,要求参与人必须获知充分的相关信息,而保密减少了公众可获得信息的质与量,使公众参与陷入步履蹒跚的困境。在座的如果是某个公司的董事会成员,都知道董事会发布指令和规则的能力受到它做出决定时相关信息多少的限制,管理层懂得其中奥秘,常常试图控制信息的流向。[12]而我们常常说责任政府,政府应该对公众负责。如果要实现公众有效的民主监督,公众应该获知必要的信息,了解政府行为的替代进路,以及可能导致的相应后果。一般的,政府中人拥有的政府决策的相关信息要比政府之外的公众多许多倍;就好比公司管理层掌握的关于公司市场、前景和技术信息要比公司的普通股东多许多倍一样,比公司之外的消费者更要多得多。
问题在于,公众已通过赋税等方式支付了政府信息收集所耗费的成本,那么谁拥有这些信息呢?是成为政府官员的私家收藏,还是为公众所普遍的享有?我认为公众为政府官员收集的信息负担成本,故信息理应属于公众所有;这和政府的桌椅及建筑设施以及其他固定资产为公众所有是类似的。我们今天都强调知识产权的重要意义,而政府产生、采集和处理的信息如同可授予专利的发明一样,同样具有知识产权权利性质。将知识产权权利为私人利用占有,与盗用其他公共财产为私人所占用的危害严重性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尽管这样一个类比也许并不是十分恰当,但多少还是有相通之处。
有人也许会说,在言论自由制度已经确立的自由社会里,政府对其信息保密并不会带来太大的损失,因为毕竟还有其他的相关信息来源。但实际上,在现代民主社会里,信息在政府有效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只有确保言论的自由和独立,以及来自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和智囊团的独立,才有可能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对政府有效制衡。问题就在于许多情况下,政府官员掌握的信息是即时性的最为重要的核心信息,如果政府官员将这些信息秘而不宣并钳制言论自由,那么公众实际上就无计可施,也找不到有效的替代进路。
所以在此需要重申的是,公开是公共治道的必备要素。Albert Hirschman将退出和发言(exit and voice)作为规范机构组织的两种机制装置。[13]而对于公共组织而言,通常并不适用退出机制,更多的还是依靠发言机制。在私人化的市场领域,一个公司如何运作组织,是否保守相关秘密,并没有太大区别,作为消费者,他不会去关心公司如何组织生产如何运作,他只会去关心你生产的产品是否物美价廉。对于企业本身而言,他常常缺乏披露所有产品品质信息的必要激励,所以政府常常对其给予来自外部的信息公开的要求和约束,[14]比如要求企业广告必须真实,企业借贷融资时必须披露相应信息,并服从反欺诈法律的有关规定。但总体上讲,企业的运作依然主要是依赖包括信誉机制在内的市场机制起作用。
但很多时候公共组织并不受同样的市场机制所调整,它主要通过对政策议题的讨论机制来实现政府治道的良好绩效。因为在政府部门对许多领域的事务都实行了垄断,在这种情况下退出机制就不再起作用。打个比方说,如果一个社区里只有一个医生,却有许多病人,这时候如果医生的处方不能治好病人的病,医生往往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试图将此归咎于病人的责任,指责病人没有按照医嘱正确服药。但是当有不止一个医生,存在竞争的情况下,一切都大相径庭,这时即使是因为病人没有遵照医嘱服药,而导致治疗效果不佳,病人依然可能将责任归咎于医生,医生的名誉也受到损害,病人通过“退出”机制去接受其他医生的诊疗。当只有一个医生存在的时候,垄断出现了,他会尽量控制信息的导向,他会发布有关信息来告诉病人我的诊疗方案是正确的(即使无效,因为安慰剂效果病人也往往感觉到有效),他敢于隐藏信息,因为他知道这里不存在竞争,退出机制也不起作用。
在所有的组织中,信息不完全都可能招致经济学家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就企业而言,经理人和普通股东的立场肯定会有不同;类似的,在公共部门经济领域,作为管理方的政府和作为被管理方和服务对象的行政相对人,立场也肯定有不同。在今天的现实语境中,退出机制的缺乏会使得代理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严峻。显而易见的是,通过提高信息质量,缩小保守信息秘密的范围,将有助于克服代理问题带来的问题与后果。
四、保守信息秘密的诱因
我认为以上的这些论述足以构成信息公开的充分理由,但事实上应当为公众服务的所谓公仆却更愿意保守信息秘密。保守信息秘密的理由之一,就是政府官员宣称他们害怕信息公开之后为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或者为特定利益集团实现其自身利益服务。但这正是民主面临的两难选择,信息公开和公众辩论机制确实也有它的不足,不过我们确实找不到更好的替代进路。[15]同时我们都认为应该让选民而不仅仅是决策者做出决策,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向选民公开更多的信息,以便他们更好的对决策质量进行评估呢?
政府信息公开有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表明,保守信息秘密很有可能是为了满足政府官员以及相关特定利益集团的隐秘目的和诉求。在此我将作进一步的分析。
有两个原因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原因之一,就是保守信息秘密可以使得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免于因犯相应的错误或过失而被提起诉讼。如果政府某项政策没有能够达到预期效果,政府官员往往会说要不是这项政策,情况会变得更糟。我们都知道人性是易于堕落的,政府官员往往宣称自己一定会尽职尽责,他们给出的理由似乎十分充分,就是公众能够对我们的行为做出最好的评判,对我们的过失加以猛烈的抨击。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在信息公开程度很低的情况下,公众评判政府官员行为好坏优劣的主要依据就是相应的行为结果。在此情况下,如果行为结果好,不管官员履行职责与否,公众都会赞誉官员尽职尽责;而当坏结果出现时,不管结果与政府官员的作为和不作为是否有关联,官员都会受到公众的抨击与责难。公开更多的信息,可以使得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价值进行更好的评判。
政府官员保守信息秘密的第二个原因,就在于保密给予了特殊利益集团施加更多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机会。在某些社会里,这表现为赤裸裸的腐败与贿赂。但即使是在反对腐败和贿赂的社会里,政治家依然需要竞选资金以追求当选和连任。那些提供给政治家资金的利益集团更多时候并不是基于他们宣称的增进公共利益的目的,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认为支持他们的一方当选后,他们有可能多多少少的影响政策的走向,提高自己的收益和利润率。正如Brandeis法官所说“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保密永远都是腐败的基础, 它削弱了公众对民主国家的信赖感。
以上是对公开化的经典论述,我今天还想论及的是,信息的缺乏,和其他人为制造的稀缺性一样,都导致了寻租。寻租问题已经得到了人们长时期的关注,这里存在一个不健康的动态循环怪圈:政府官员有着制造信息秘密的激励,因为籍此可以获取租金。秘密的出现使得新闻舆论对公开的要求呼声更加强烈,官员有时仅仅向那些和自己相处“关系”好的新闻界人士才公开信息,用这种方式来收获租金。在此背景下,不仅公众本应享有的及时获取相关信息的权利被剥夺,而且政府官员有可能利用他们对信息的控制权,基于自身的利益来扭曲信息;政府官员会这样做,多少让我们感到匪夷所思,但这样的事情其实每天都在发生。传媒与政府的关系就这样被扭曲,如果有新闻记者有勇气披露这些,破坏两者之间这默示的契约,那么其所在媒体就很有可能被政府排斥在主流传媒之列。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再有勇气有独立自由思想的新闻业主,也只能别无选择的把惹祸的记者解职。我们无法想象,当记者写作了稍微过头的批评文章,就会被批评对象限制其信息获得权时,新闻媒体怎样来进行有效的舆论批评和监督。这种畸形的关系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也削弱了公众对媒体的信任程度。
为了更好的说明政府官员存在信息保密的激励。我们可以拿一个公司作比方。公司的管理层总是试图获得信息控制权,限制那些小股东获得信息的能力,从而他们可以更有效的决定公司事务,对小股东发号施令。管理层通过向外围小股东制造不对称的信息壁垒,来增加他们的管理租金,当然这是以那些分散的持股人资金投入为代价的。当管理层制造出更多的信息不对称,小股东对公司事务就更加缺乏决断力,更感受到管理层决策的重要性。事实上,信息披露的匮乏增加了交易成本,使得股东改变管理层构成的成本更为高昂。同时由于管理层之外的股东信息上的劣势,也就意味着他们提出的决策建议更有可能把态势变得更糟。信息不对称使得公司管理层有着比较竞争优势。
基于同样的原理,保守秘密削弱了选民有效参与民主过程的能力。当选民对自己的观点有信心的时候,他们更愿意独立的不受党派团体影响,进行独立投票。但反过来这需要他们能够获知必要的信息,这同样需要成本。当然绝大多数选民不是完全自私自利的,如果那样理性化的参与政治过程也就无从谈起(毕竟公共物品也是公众的财富),但是就他们每个人而言,依然存在一个阈值,他们愿意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而为此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度的。保密增加了信息成本,这使得许多选民在自身没有什么特殊利益的情况下,不再积极参与民主过程,而将许多相应的领域留给了那些特殊利益集团。不仅利益集团可以在保密外衣的遮蔽下行邪恶之事,保密本身也使得那些本来想通过参与制民主对特殊利益集团进行监督制衡的公众裹足不前。这充分说明了“公共信息制度”在促进公众福祉领域的重要意义。我们倡导必要的新闻自由,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那些被“俘获”的或者哈巴狗般的媒体,更需要那些针砭时弊反映公意的媒体,他们扮演者类似于国会总是唱反调的反对党的角色;同时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社会公益组织,吹响为公众奔走请命的号角,将特殊利益集团的隐秘活动曝光。
信息的保密也使得许多本来在政坛可以有一番作为的人心灰意冷,使得他们不仅对投票程序的公正性前景产生了怀疑,他们担忧自己即使上台也未必能使局面有起色。由于政府信息的保密,他们害怕自己热情满怀的上任之后,面对的是比所公布信息糟的多的财政预算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原先所有的雄心壮志都只能付懂流水,他们能做的,仅仅是煞费苦心的去尽量实现预算的平衡。
五、信息保密带来的消极后果
前面我们给出了政府官员在明知公开化是民主过程核心理念之一的情况下,依然对保密满怀热情的几个原因。之所以这样详细的阐述这个问题,因为洞悉了政府保密的激励,有利于我们彻底根除废止它实现信息公开,也使得我们对信息不公开的危害有更加深刻的感悟。
前面提到,信息保密培育了滋养特殊利益集团的肥沃土壤;增加了管理租金,加大了交易成本;使民主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大打折扣;使得媒体舆论无法形成对政府滥用职权的监督制衡机制。同时信息保密还有更大的危害:为了保密,政府常常把决策人员限制在一个小圈子范围内,那些本来可以提供深刻洞见的人被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这样的决策质量因此也就差强人意;而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随着政府决策失误的增多,政府官员怕承担责任,转而寻求自我保护,信息就更不敢公开,决策圈子变得更小,决策质量也就每况愈下。
信息保密还有一个负面作用,那就是不当的转移了公众的视线和精力。由于诸多重要信息为政府所保密,公众无从知晓更无从发表意见。而相应的,对堕胎和婚姻问题进行讨论发表见解所需要的信息,要比对复杂经济态势进行评判所需的信息少得多,但是我们并不能说后者就不重要。信息保密不仅使得许多重要的公共政策没有接受公众的充分讨论和评论,还使得公众舆论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更不重要的细枝末节问题的讨论上来。
截至目前更多的研究论文集中论述的都是信息保密对政治过程带来的消极影响,但这里要论述的是信息保密在经济领域的负面影响。今天我们都知道质量更高更及时的信息可以使我们更好更有效率的配置资源,进而调节经济运行。今天信息产业不断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员工从事着信息的收集、加工整理和发布的工作,这也印证了信息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员工从事的工作,竟是设法收集发布那些政府部门本应公开却秘而不宣的有用信息。企业也许有理由主张对自己的某些信息予以保密,因为信息公开以后有可能被竞争对手利用;但是政府部门从公众身上采集的公共经济和生活信息,有什么理由不向公众公开呢?政府对信息的垄断不利于市场资源的配置,也阻滞了市场的活力。
信息保密的最为消极的经济后果,还是因过度保密导致腐败的滋生,这样的事例已经屡见不鲜。目前已经成立了一个“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跨国非政府反腐败组织.。世界银行1997年的《全球发展报告》中也指出了腐败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诸多不良影响。应该看到,官员总是有着保密的强烈欲望,我们要想克服信息保密带来的诸多政治的和经济的消极影响,那么在公共行政的制度设计中,就必须牢记以下精髓:我们的信息公开范围决不能被政府官员的主观意愿所局限,而是要超出这个范围,将其尽可能的拓宽。
六、信息保密的实施
我们已经知道政府官员保密能够给自己带来那么多好处,所以许多国家的政府保密范围远远超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变得十分宽泛,也就不足为奇。但尽管政府作为整体有着保密的偏好,但对于某一个特定的政府官员而言,却未必如此。就特定事项的信息保密而言,其实可以视作政府部分官员的合谋行为,而其中的任何一名官员都有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将信息向特定的媒体或利益集团,收获因信息稀缺性的租金。但在这里信誉机制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接受秘密信息的一方必须向该官员保证不向公众公开此信息,如果它敢公开,那么这个信息源以后就断了;同时如果信息通过此链条变成公共知识,政府其他的官员就很可能联手“惩罚”这个泄密官员,剥夺该官员的信息获得权,或者以其他的方式给予他冷遇或排斥。
这也说明了传媒和政府之间有着微妙的共生关系。但是正如在任何信誉模型中,确定性的博弈都依然有着被拆散的可能。从政府官员的视角,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闻记者的信誉,他们不知道记者能否一直做到守口如瓶,因为新上任的官员很多时候会成为传媒品头论足的焦点,在许多时候他怕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因而还是更愿意保守信息秘密,对媒体秘而不宣。
信息保密还有一个社会学上的仪式功能。许多俱乐部(Club)都有着保密的仪式,他们共享某些信息秘密,但却向外界保密。[16]某种意义上秘密成了辨别俱乐部成员与外界成员的一种标志和纽带。俱乐部通过自身的“惩罚”机制使得每人都要服从信息保密的拘束;同时当俱乐部的大多数人都奉保守秘密为行为准则时,个人也就形成了相应的伦理价值判断,他们会觉得保密应该是自己的一种责任。俱乐部尚且如此,政府的信息保密也有着类似的社会学上的仪式功能。
但近年来,信息保密观念在不断弱化,原因之一就在于公务人员越来越认识到信息保密不仅与民主过程相悖,而且提供了更多腐败滋生的机会。同时人们逐渐认识到了信息保密博弈的性质,发现即使公认泄露了信息,被追究的概率也很小;同时还可以利用公务人员和传媒的特殊关系,进行抗辨,从而免于追究与处罚。事实上,越是与传媒有特殊利益关系的官员,越虚伪的赞成信息保密,因为信息越是保密,他们越可以通过向特定传媒发布信息收获稀缺性租金。信息公开无疑断了他们的财路。这样看来所谓的“完全”保密均衡是那样的弱不禁风,在这样的信息保密和披露博弈中,并非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而局部的信息保密均衡造成的却是对民主过程的扭曲和破坏。
七、信息公开的例外
今天,即使是那些要求保密的政府官员,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阐述保密的重要性。他们无法反对公开化,但是他们会阐述过度公开(excessive openness)所带来的问题。而我要说的是,今天即使西方最为公开化的开放型政府,信息公开也不是太多,而是还很不够。但是我依然承认信息公开确实有一定的限度,在此,我试图将他们的论点加以归类整理如下。
(一)隐私信息的例外
这些和个人或机构有关的隐秘信息,构成了信息公开的最重要的也是最令人信服的例外。政府在履行其行政职责的时候,收集了大量的个人隐私信息,如收入状况、健康资料等。但是本文所论述的政府信息基本上都不再此范围内。
(二)机密信息(Confidentiality Exception)
与以上隐私信息多少有些类似的是机密信息,这些信息的公开会给后续的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比如有的国家会寻求世界银行的帮助对该国的银行体系进行重整。但在这样的过程中,世界银行会发现该国银行系统的种种薄弱之处。如果该国知道世行会将这些信息公开出去,那么该国会有强烈的动因拒绝寻求我们的咨询和帮助。再比如医生应该对病人的健康信息保密,律师应该对当事人的信息保密,但在公共部门领域,因机密信息而可以享受信息公开例外的情况,被限定在一个相对十分狭窄的范围内。
(三)国家安全的例外(The National Security Exception)
战争时代保守国家安全秘密的意义为人所共知。当一个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它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以增加获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而战略进攻很多时候就在于出其不意,在于敌人无法得到必要的信息预警,也无法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问题在于国家安全的例外有时会扩展为与国家安全毫无干系的领域,从而作为掩饰错误的工具。在五角大楼公报对越南战争的审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面临是否还要将越战打下去的难题,而此决定所依赖的至关重要的信息在于战争的进展情况。但此信息对于感觉到的敌人也有价值。
今天所担心的是在国家安全领域之外对政府信息进行了过多的保密。
(四)拥挤剧院中的“纵火”
有时候信息公开会带来生死攸关的后果。而重要的,并非信息是否公开的问题,而是信息如何公开的问题。霍姆斯法官对表达自由权利例外的著名判断,是建立在拥挤剧院中“纵火”引起的恐慌基础例证之上的。
对经济事务而言,这样特别例外情况是以特定形式表现出来的:对诸如货币政策之类事务的公开讨论可能会使得经济动荡。有趣的是,那些持此观念的人却多是对市场的坚定拥护者:尽管他们对市场有充分的信任,但是有证据表明他们相信市场会为不相干的“噪音”所影响。当然,如果认为所讨论的或公布的信息是相关信息,那么对经济基础有影响,则要求尽快公布信息以使得更有效率的配置资源。
就货币政策而言,对中央银行是否应秘密行动,有着广泛的争论。他们是否应将自己的工作进展公开,可以容许有什么样的延迟,对细节的公开应该到什么程度?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市场的簇拥者赞美市场“发现”价格的功能,但公债市场上发现价格的功能,很大程度上在于判别出中央银行银行家们在想什么、可能要做什么。除了这非正式的“舞蹈”之外,难道中央银行就不应该直接披露相应信息吗?如果市场确信这些信息具有价值——成千上万的人见证着注视着中央银行的行为——难道政府就不应该及时公开这些信息吗?显然,中央银行(以及它们的政府)在自己运作过程中,并不那么情愿信息公开。
没有理论或实证表明更加充分更为及时的信息公开和讨论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实际上,由于信息早晚总要被公开,当下试图将信息密闭起来的程序,将使得定期公开的时候要公开大量的信息。而经济要更加稳定的运行,经常性的作一些微调而不是大规模的调整,因此稳定的信息流将使得经济有可能变得更加稳定。在信息持续公开的情况下,人们不需要再对某一个时段给予特别关注,也可以减少事后对资源配置的调整。
类似的,在英国决定增大中央银行的透明程度之后,也没有经济不稳定程度增大的迹象。
经济领域的保密不仅增加了总体不稳定性,而且在许多国家,也降低了公众对政府的信赖程度,成为导致腐败的重要因素。
对于充分信息公开和讨论会导致市场不稳定的论断,充其量只不过对信息公开的时机与方式有影响,并不能作为将公共讨论无限期拖延的藉口。回到前面那个“拥挤剧院中纵火”的隐喻:没有人会认为如果有人知道剧院着火,不应告知大家有序撤退的方式;同时我认为,在火灾结束之后,没有人会反对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以确证火灾的成因,是否有死亡或严重伤害,以探明在未来如何避免类似灾害的发生(如剧院结构以及设计方面)。同时没有人会认为,因为有可能引起剧院中行走观众的“不安”,就不设置灯光指示的出口标识,以指示有火灾时候如何撤离剧场——我们知道不论剧院的设计构造多么完美,还是存在火灾的可能。
对信息问题而言,有人害怕信息会给市场带来不安定。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难道不应对民主过程有足够的信心,相信市场能够识辨那些不和谐的声音,对基本判断加以评价,查明事实。
我并不相信在寻求民主公开和经济稳定增长之间,会存在实际的平衡。两者之间如果发生冲突,我坚定的认为应将民主过程的公开价值置于重要地位。
民主社会必须去寻找并找到在复杂技术性决策中的程序,以反映共同的价值与专业知识。但由于产业集团可能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份额,所以要防止决策仅仅反映了产业集团利益,因而决策要尽可能公开,并将其置于民主过程的框架之下。实际上,对独立管制机构而言,它拥有更多专业知识,更可能绝缘于政治过程的浮沉变迁之外,因而透明公开就显得更为必要。
(五)公开的契约应公开缔结
每个小学生都会学的一句美国格言,是一战噩梦之后伍德罗·威尔逊的格言“公开的协定应公开缔结”(Open covenants openly arrived at)。在80年前,公开成为国际性的公共议题,普遍认为一战中和一战之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秘密协定秘密缔结,但在此前和此后,都没有对公开问题给予过多从容考虑的热忱。其担忧在于开放的讨论会抑制观点的自由表达,在微妙的妥协与复杂的联合居于成功民主过程核心以达成解决方案之前,使得特定利益群体已占据优势的地位。保密为棘手谈判成功所必须。
我认为上段的观点具有一定意义。但问题在于,提议早晚要提交公众讨论,特殊利益群体还是有机会来破坏已形成的任何联盟。实际上如果进一步提高公开讨论程度,某种特定观点就很难占今天这样的权重,每种观点都可以得到认真考量,接受全面详尽的审查。于是这又变成了一个时机问题:在决策过程中,也许要存在一定阶段的保密,但最终观点和争点还是要加以充分公开。
从实践角度,我发现这蕴藏了两种危险倾向。第一,也许总是找不到合适的公共讨论的时机,“微妙”的时刻一个接着一个。第二,公众常常受到轻慢的对待:让他们知道提议的内容,却不让他们知道其前因后果,这就好比孩童无法洞悉父母的争吵一样。但公众知道很少有几件事情是黑白分明的。在公共政策领域,常常蕴含着对具相当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事务的判断。
(六)破坏权威,抑或家丑不可外扬(Don't air your dirty linen in public)
有人认为对公共事务的讨论,特别是对其中不确定性和错误的讨论,会弱化公共机构的权威,构成对民主制度的最严重侵害。这与独裁主义政制贯常使用的论述相类似。而相反的,我认为如果政府诚实的对待公民,对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信赖将会增加而不是减少。我们都知道Alexander Pope的不朽箴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To err is human),人性的不可靠成为我们制度设计的基础,这也是我们需要有监督制衡机制的原因。我们都知道信息不完全(imperfect information)的存在,信息不完全在我们必须做出的重要决策中,有时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假定所有机构都是可以信赖的,或对政府行为应有完全的信赖,这公然与现实相背离,只有那些情愿被愚弄的人才会这样想。承认政府机构会犯错误,并致力于民主过程中的公开讨论,这不仅反映了政府机构对自己的信心,也增大了人们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
当然,如果缺少一定的忠诚度和组织结构,组织就无法运作。[17]民主过程的运作有赖于功能良好的组织,这就引出了最为棘手的问题。要使得民主制度完全起作用,就必须增大政府机构的信用程度,这就可能要对完全公开予以一定限制。
其间至关重要的问题又是时机问题。某个决定一经做出,任何政府都要设法让他人对其观点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如果决定做出之前的分歧通通面向公众公开,也许不是最有效的选择。更直白的说,一个人可以视政府为团队。在决策做出之前,至少需要在团队内部的开放讨论。当然政府中也存在职能分工,而且在公共领域可能几个机构会有不同的利益所在,但每个政府机构在其职权范围内都为决定担负完全责任。离开了与其权限有关的各政府部门的有效参与,作为团队的政府将无法顺畅运作。当一个决定做出之后,各部门应依据达成共识的战略开展协同工作,设法使得他人相信其行为的适当性。
重复我前面所说的,决策过程中的更加公开,对不同意见的考虑,有可能赢得公众更多信赖。程序公开可以保障决策不为利益集团所左右,保证决策对所有重要因素、对各方面利益都加以关照。当然采取行动的时候,还是存在对事实的判断和对利益的衡量,当然某种意义上民选政府就是要来回应如此艰难的选择。
但即使当政府做出如此决定之后,最终还应对行为的效果做出诚实的公开的评判,这将是政府从实践中学习进步的基础。
跟前面部分的论述一样,对“弱化政府信赖程度”和“作为团队的政府”等的担忧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它们常常被夸大其辞,走的太远。前述在职官员的保密激励使得机构领导人常常倾向于调用这些论说,将此作为保守秘密的理由。
在公共领域中,每个人都要对我们的公共话语与私人话语加以权衡,特别警惕过度保守秘密倾向的出现。而我自己对民主过程的信任,使得自己深信应进一步拓宽信息公开范围,这并不会象有人所宣称的那样有太多削弱政府机构权威的风险。我的前任罗纳德·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Martin Feldstein先生,对巨大财政赤字增长的后果作了如实的讨论,尽管他并没有能成功的改变政策,但他在公意形成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最终导致了1990年代的赤字减少。我相信这样开放的讨论最终将增加公众对民主过程和制度的信赖程度。
八、信息公开制度的实施
我已对提高政府透明度开作了不厌其烦的论述。透明度的提高是如何实现的?同时我也试着说明了政府存在强烈的保密激励。保密的激励是如此巨大,常常足以打消出台信息公开规章的念头。如果要求正式会议必须公开,那么所有决定就有可能在非正式会议上做出;如果要求书面资料必须公开,那么政府就存在尽量少留下书面资料纪录的激励。正是由于这些限制,所以必须对建设公开文化予以重视。其假定就在于公众应了解并参与所有集体行动。我们必须确立公开的理念,坚信公共机关官员所拥有的信息都为公众“所有”,将其用于私人目的,无异于对公共财产的偷窃。
信息公开存在少数情况的例外,但对这些例外的范围应予以高度限制,对例外范围作尽可能狭窄的界定。信息公开例外范围的确定应交付公众讨论。
196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信息公开法,建立了公众知情权法律制度的框架。原则上,这部法律保障任何公众都能获得公共领域的任何信息,规定了基于隐私的狭窄的例外情形。但这样的立法只能说是部分成功的,除非拥有对公开的切实保障。政府官员会小心翼翼的写下记录,同时还是存在“嘴对耳”(mouth-to-ear)的秘密,确切的说他们还是不情愿将重要信息向公众公开。
保密的一个强烈激励在于为利益集团的运作披上遮蔽的外衣(包括那些被影响的)。对选举中捐助的公开是非常有意义的,这至少使得选民更加敏感,对诸如烟草捐助改变立法结果之类的事情予以警觉。但我必须承认尽管美国对信息公开作了严格的规定,但利益集团似乎还有相当的运作空间,某些情况下甚至比没出台这些规定还要糟。
在信息公开行动中,新闻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有时新闻界也是“保密阴谋”(conspiracy of secrecy)的核心部分。新闻界必须承诺自身运作的公开。但期望他们将其政府内部的信息秘密来源,或发布相关信息特权都公开,是不太可能做到的。但对新闻报道机制应予以更多的报道。
同时非政府组织在帮助建设行政公开文化,制约政府官员保密倾向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九、结语
长期以来大赦国际一直在致力于确保所有的政府都能对基本人权加以保护。在人格尊严方面,它发出了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声音。公开透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机制之一,在保密的外衣之下,个人权利经常性的被侵犯。
长期以来我一直关注人权和人格尊严问题,用富兰克林·西奥多·罗斯福的话说,要有“免于饥饿”(freedom from hunger)的权利。当一个人看到他的孩子因饥饿而死或他/她的女儿仅仅为了生存而卖淫时,是谈不上人格尊严和基本权利的。毫无疑问的政府的决定与基本人权的保障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这些决定应公开做出,并得到被影响者的开放式积极参与。我深信公开和参与无疑将影响做出决策的质量。
从制度层面考察更多信息公开的正当性,公开可以减少权力滥用的可能性,透明度的提高是良好治理的核心要义。一个有力的例证就是透明度的提高可能会避免冷战时代的极端对立。我相信通过进一步公开,会比一味保密仅仅依赖专家智慧,做出更好的决策。冷战的终结真实的反映了保密文化的失败,也弱化了保密制度继续存在的意义。也许冷战时代最具讽刺意义的是,为了保持民主和民主价值,我们选择了破坏民主程序的政策。保密文化好像病毒,从一个政府传染到另一个政府,它蔓延到甚至与国家安全毫无干系的领域。
但是我依然相信透明度的提高有其内在价值,公众有基本的知情权。我已经尝试从多个角度对这一基本权利加以阐释:公众为信息支付了费用,而政府官员为了他/她的私人利益,或仅仅追求良好的新闻效应来对信息加以处置的话,这是与偷窃其他公共财产一样的盗窃行为。虽然我们都认识到集体行动的必要性,集体行动对个人自由的影响,我们有知晓集体行动中权力如何运作的基本权利。这似乎可以视为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达成的默示契约。当然这存在例外,我对这些例外已作了详细阐述,但我要说明的是,至少应对例外情况的范围予以限制。
同时对我而言,如果政府机构更少直接对公众负责,那么其行为的公开透明就变得更为重要。类似的,政府机构越是独立,越少承担直接的政治责任,对其透明程度的预期就越高。公开是对公共信托责任滥用的最为重要的制约机制之一。
我们处于一个令人激动的年代。冷战的终结给予了我们机遇,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保密与公开所扮演的角色予以重新审视。同时,新技术提供了信息更有效为政府与被统治者所分享的机制。今天的选民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了解更多的信息。进一步的,与一百年前相比,受教育程度有了难以想象的提高,这是的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及时阅读可得信息并对之予以评价。
我们还要向前迈进一步:政府应承诺进一步提高透明度,促进对话和开放讨论,戒除形形色色的保密。尽管我已经描述了所有政府需遵守的公开法律的轮廓,但我也认识到信息公开立法的局限。保密的激励太过巨大,裁量行为的范围太过广阔。因此我要强调建构公开文化的重要意义,类似大赦国际之类的组织将在其间发挥重要作用。这样的公开并不一定能保证永远做出正确的决定,但它将是民主过程形成演进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对个人真实的授权,使得他们能够真正参与到对自己生活将有深远影响的集体行动决策之中去。
参考文献:
[1] 作者斯蒂格利茨因其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对市场经济进行的研究,同乔治·阿克劳夫、迈克尔·斯彭斯分享了200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生于1943年,196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先后就任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教授,并曾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获奖公告中,认为斯蒂格利茨将信息不对称理论运用于保险、财政、资本、信用市场等的研究,为信息经济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2] 译者现为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
[3] Sen, A. 1981. "Ingredients of Famine Analysis: Availability and Entitlements." (饥荒分析的要素:可行性与权利)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6(3), August. 433-64.
[4] Moynihan, D. P. 1998. Secrecy: The American Experience(美国保密的实践). Yale University Press. September.
[5] Stiglitz. 1992. "S&L Bailout," In The Reform of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Disciplining the Government and Protecting Taxpayers, J. Barth and R. Brumbaugh, Jr. (eds.),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6] 对此全面的讨论可参见Bok, Sissela 1982. Secrets(秘密). New York: Pantheon.
[7] 对此的综述,可参见Emerson, Thomas 1967.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the First Amendment(面向第一修正案的一般理论). New York: Vintage Books; Emerson, Thomas 1970. The System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表达自由体系). New York: Vintage.
[8] Padover, Saul, Ed. 1953. The Complete Madison(完整的麦迪逊). New York: Harper.
[9] Mill, J. S. 1961 (1859). On Liberty(自由论). In The Philosophy of John Stuart Mill. M. Cohen Ed.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85-319.
[10] Mill, J. S. 1972 (1861). Consideration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代议制政府). In J.S. Mill: Utilitarianism, On Liberty and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H. B. Acton Ed. London: J.M. Dent and Sons.
[11] Bagehot, Walter 1948 (1869). Physics and Politics(物理和政治). New York: Knopf.
[12] 参见马克思·韦伯对官僚制度中保密作用的论述,see Weber, Max 1958. Bureaucracy(官僚制度). In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H. H. Gerth and C. W. Mills Eds. New York: Galaxy: 196-244.
[13] Hirschman, Albert O.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退出、发言和忠诚:对公司、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4] 对信息披露的市场激励,以及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可参见Stiglitz, J.E. 1975. "Incentives, Risk and Information: Notes Towards a Theory of Hierarchy(激励、风险和信息:对科层理论的评注),"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6(2), pp. 552-579;Stiglitz, J.E. 1975. "Information and Economic Analysis(信息和经济分析)," In Current Economic Problems, Parkin and Nobay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7-52.;Stiglitz, J.E. 1998. The Private Uses of Public Interests: Incentives and Institutions(公共利益的私人利用:激励和制度).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2:3-22, Spring;Grossman, S. 1981. "The Informational Role of Warranties and Private Disclosure about Product Quality."(担保中的信息作用和产品质量的私人披露) Journal of Law and Eocnomics Vol 24:461-484.
[15] 社会日益面临复杂的技术性问题,如何将专业技能、民主责任和代议制度加以整合,尝试性的讨论可参见Stiglitz, J.E. 1998b. "Central Banking in a Democratic Society"(民主社会中的中央银行) De Economist (Netherlands); 146, No. 2.
[16] 参见前引Bok书第二章“Secret Societies”(秘密社会)。
[17] Peters, C. and T. Branch 1972. Blowing the Whistle: Dissent in the Public Interest. New York: Praeger.
编者注:本文原刊于《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转载自“规制与公法”(ReguLaw)公众号。编辑:郭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