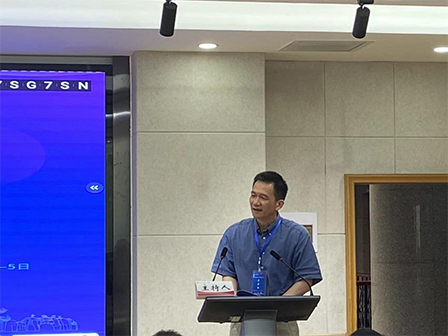传统中国乡村的契约精神
书刊 · 2014-12-08 00:00
返回正是因为乡民对于确认相互间的权利关系有明确的意识,我们才会在今天看到如此大量的契约在南方各地保存下来。订立契约、保存契约,这些行为本身就彰显着十八世纪以来乡村社会中存在着的某种“契约精神”。 在学者笔下,...

正是因为乡民对于确认相互间的权利关系有明确的意识,我们才会在今天看到如此大量的契约在南方各地保存下来。订立契约、保存契约,这些行为本身就彰显着十八世纪以来乡村社会中存在着的某种“契约精神”。
在学者笔下,传统中国乡村的形象并不“稳定”。1930年代费孝通撰写《江村经济》时,开弦弓村给人的印象是灵活的手工业与金融借贷,但同时存在着产业凋敝的危机。由开弦弓村所代表的那种商业与小农经济灵活结合的传统乡村形象,在1950年代之后相当程度地被淡化了。“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在很多时候成为史学界的一个标准论述,甚至到今天还颇有影响。
海内外对这套论述的质疑很早就开始。厦门大学的傅衣凌教授很早就注意到明末江南高度发达的经营农业。1960年代,日本的社会经济史学者也在江南文献中爬梳农业经营卷入贸易流动的实态。其中著名的案例,如明代常熟的谭晓:
谭晓,邑东里人也,与兄照俱精心计。居乡湖田多洼芜,乡之民皆逃而渔,于是田之弃弗治者以万计。晓与照薄其值,买佣乡民百余人,给之食,凿其最洼者为池,余则围以高塍,辟而耕,岁入视平壤三倍。池以百计,皆畜鱼,池之上架以梁,为茇舍,畜鸡、豕其中,鱼食其粪又易肥。塍之上植梅桃诸果属,其泽种菇茈菱芡,可畦者以艺四时诸蔬,皆以千计。……室中置数十匦,日以其入分投之,若某匦鱼,某匦果,入盈乃发之。月发者数焉,视田之入又三倍。(《常昭合志稿》卷四十八)
谭晓能够雇用乡民百余人,利用价格波动购置土地,还设计合理的种植结构,这样的农民无论怎么看也绝无法称之为“封建小农”。谭晓如何购置这些土地,文献中只是一笔带过,事实上,明清以来乡村中的地权结构,最令历史学者头痛。
西方法律传统中,产权是一种排他性的独占权利。而中国乡村中,“一田两主”是普遍现象,即一份产业有两个甚至多个权利享有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辑录了不少南方各省的情况:大买、小买、田面、田底、粪土、顶首……光是描述地权交易内容的称谓就纷繁复杂,眼花缭乱。
与“封建小农”并行于世的另一种标准论述是“土地兼并”与“地权分化”。翻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各种涉及乡村地权问题的著作,不论支持或反对,土地兼并、地权分化等描述都显著地占据关键位置。
近代中国是个由于“土地兼并”与“地权分化”激化了矛盾的社会吗?这问题便与地权结构有关。本来一块土地,有人买下,再出租给别人,出租的人便是地主,承租人则是佃农,这是简单易懂的道理。不过在中国乡村里,土地可以分拆成田底、田面分别交易,拥有田底者为土地缴税,拥有田面者佃人耕种,佃农租来之后又可再转租,甚且再分拆出售。至此,已至少有三四人享有这块土地的收益。这还不算完,土地出售,也不是卖完了事,卖后可以回赎(称为活卖或者典、退),除非契约上约定不可以回赎(称为绝卖)。徽州的不少契约为表示这一层意思的真切,要写作“断骨”。卖完之后,卖家往往过几年还要再找买家“加找”,就是再加一份钱给他。至于用土地做抵押,期限的算法,利息的算法,就更花样百出。
1950年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史学者与法制史学者,都致力于更好地解释这些复杂的地权交易现象,所依凭的主要材料则是契约文书。
契约文书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材料,从傅衣凌先生开始。其大规模收集,则是1950年代由郑振铎先生主持抢救收购徽州文书。1939年,因抗战关系,傅衣凌先生在永安福建银行经济研究室工作。在永安黄历乡,他发现了一箱明中叶至清末的契约文书。傅先生是社会学出身,因而对此材料非常敏感,据此写出他的著名论文《明清时代永安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清代永安培田约的研究》。
1957年,郑振铎先生委托书商韩世保在安徽屯溪收购古籍(即原徽州地区驻地,现黄山市市区)。韩世保在收购古籍之外,又向郑振铎报告,当地不少契纸被收购做烟花爆竹的纸芯。郑振铎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即呼吁抢救收购。1958年,屯溪旧书店的余庭光担负此任务,前往徽州各地收购契约文书,此后十余年间,经他手运往各图书馆、高校、研究机构的徽州文书据说有数十部汽车之多。
这样,在1950至1980年代,社会经济史学界讨论明清以来乡村地权结构的主要材料就是徽州文书。
在这一时期,契约文书的收藏基本是以单件为单位的。从研究角度来看,单件契约只能反映交易形态历时性的变化,以及每一件契约之间的交易内容与交易形态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的社会背景很难明了,进一步说,历史学家更希望了解,这类文献产生于怎样的社会结构,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发挥怎样的功能。缺少有机联系的单件契约在这方面就显得解释力不足。
近些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一方面,越来越多学者深入田野收集材料,契约文书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在收集时就得以明确;另一方面,文书与当地社会的有机联系也成为文书整理、出版的一个重要考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针对传统乡村地权交易的新解释出现了。如龙登高对“典”权提供了新的解释,认为这种中国独有的交易方式是产权分割、分化的一环,就法学中应相当于“他物权的转让”。另一引人注目的研究,则是浙江石仓研究。
石仓是位于浙江松阳县的数个村落的总称。康熙年间,一支福建汀州阙姓移民定居于此。到十九世纪初,阙氏宗族在当地从事炼铁业,获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功。2007年,曹树基教授等人在当地发现了数千件文书,包括置地购产的契约、炼铁业账簿、科举账簿等。
从契约的内容、类型来看,除涉及洗砂、炼铁部分外,石仓契约中出现的交易类型在徽州文书等材料中大多存在。但是,研究者在收集这批材料伊始,就留意记录其原始保存状态,确定每一件文书的来源,更难得的是有大量族谱材料相匹配,使得契约文书背后的社会关系网络,得以全面呈现。
石仓与徽州、福建等地一样,存在着多种多样地权交易的概念,其中最重要的如“永卖”、“退”、“讨”、“拨”等等。因为可以利用族谱确认交易者的身份,进而追踪交易的整个过程,对于这些概念的确切含义,也就有可能进一步挖掘。这些契约涉及不同类型的地权交易,最基本的是各种绝卖契,是一次性出卖土地的全部权利。但是,至少十九世纪中叶之后,石仓当地的一般做法是订立卖契的同时又订立找契。从形式上看,是买卖后再加找一次,而实际的交易是一次性完成的。更复杂的交易是退、典当、讨。“退”是地权部分转让的一种形式,在清代石仓、徽州都普遍见到契约中出现这一说法。
以退契约为代表的“不完全产权”交易反映了清代乡村中土地权利的一些特点。在现代法权观念中,无论“田面”、“田底”都是不完全的产权,甚至难以得到法律支持。但在当时农民的观念中,最看重的是从土地获得收益的权利。“股”一词经常出现在清代契约文书中,家庭分产,或者钱会集资,都用“股”表示所分得、所持有的收益。
从收益的角度来理解,无论“田底”、“田面”或者其他分割地权的方法,都可视作“股份”。占有股份的多少,则决定了从土地获得收益的多少,这是与农民的切身利益最相关的。这也可能更接近清代小农对土地经营的理解。
从现有的文书来看,石仓的阙氏宗族到二十世纪初时,土地经营已经非常细碎,每个家户所持有的土地非常少,在这个村落里,找不到真正能称为大地主的家户。当地的炼铁业到清末时就已经不能再获得大量收入,当乡民从工商业回归农业时,土地也就不再集中于若干成功的工商业者手中。经过数代的分家与土地买卖,我们在这个南方山区乡村中看到的是一个地权分化程度极低的社会,而这恰恰是这个社会基本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的时期。
徽州、石仓等契约文书的研究帮助我们建立了更多有关清代乡村土地市场的经验。在乡村社会的经济生活中,亲属关系、社会组织等等的确不同程度地约束着当地土地市场,但是,在每个普通农民的观念中,对土地、资本的权利关系划有清晰的边界。何种权利属于谁,在他们心中绝对是算得清清楚楚的。也正是因为乡民对于确认相互间的权利关系有明确的意识,我们才会在今天看到如此大量的契约在南方各地保存下来。订立契约、保存契约,这些行为本身就彰显着十八世纪以来乡村社会中存在着的某种“契约精神”。
石仓的经验还提示另一点,阙氏家族在这偏远山区能够建造华丽大屋,大量购买土地,依靠的是工商业的成功,而非所谓的土地兼并。阙氏家族在炼铁业衰落后,仍然保有不少土地,但这些土地经过数代的分割、交易,权利关系已经细碎而错综复杂,同一块土地可能被拆解为田底、田面、佃种、抵押多种收益,有多个不同的主体共同享有这块土地的收益——从某种意义上说,纯粹的“地主”是不存在的。
如果基于以上认识观察二十世纪,革命进程中对“平均地权”的追求则显得意味深长。即使不过分向前追溯,孙中山所提出的“平均地权”口号也可视作漫长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的“核心理念”之一。而在此后,不论国民政府时期的“二五减租”或共产党领导的各种土地改革,显然都是以改变地权分化的“现实”为诉求的。
平均地权,消灭地权分化,作为一个理念,的确有力推动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革命。但“地权分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现实”,似乎是有必要重新考量的问题。通贯地观察十八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的土地权利关系和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思潮,相信会有助我们领会到二十世纪中国漫长的革命进程的新意义。■
延伸阅读
《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曹树基、刘诗古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