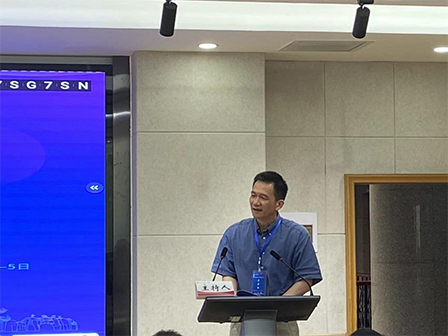《21世纪的资本》:向“世袭财富”开刀
书刊 · 2014-06-24 00:00
返回《资本》去年在法国出版,卖出了约五万本。以法国未足七千万的人口看,销情不恶。其所以没引起“识字分子”热烈讨论,笔者的解读为:法国税率已高至接近皮克迪心目中的水平(高收入个人入息税率百分之八十),法国有钱人(...
《资本》去年在法国出版,卖出了约五万本。以法国未足七千万的人口看,销情不恶。其所以没引起“识字分子”热烈讨论,笔者的解读为:法国税率已高至接近皮克迪心目中的水平(高收入个人入息税率百分之八十),法国有钱人(“百分之一”)已深受高税之苦,因此社会上对向他们课重税的提议,反应冷淡。 皮克迪提出世界各国征收统一“环球财富税”,这确是阻遏“财产世袭资本主义”的深化、纾缓贫富两极分化的良方。但这可行吗?答案是绝不可行。
从皮克迪的简历看,可以说他是神童,但说他早慧及少年得“意”,似更准确——1993年他二十二岁便获“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受聘为美国麻省理工经济学系助理教授,至1995年辞职,加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为研究员;2003年出任由他主催成立的“巴黎经济学院”教授,且于2006年被委任为校长,2007年起回校担任教授兼任法国社科高级学院(EHESS)总监至今。
香港是个贫富差距极大的国际都会,这是港英政府的政策长期向富裕阶级特别是物业发展商倾斜的结果。这种政策在回归后持续,造成“港亿万豪门比例冠全球”的事实。面对这种现象,特区政府,尤其是早非公务员而具政治任命身份的财政司司长,当然得动动脑筋,在坚持稳健理财“哲学”的同时,应该加入一点新思维,比如恢复征收遗产税、红酒税及行累进入息税制……
今年经济学界的“盛事”,莫过于英译法国经济学家皮克迪(Thomas Piketty,1971-)《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以下简称《资本》)的出版。这两三个月来,冷热传媒的读者和听众,不论西人汉人,很难不碰上谈论这本书的言论。笔者的“评介”肯定“迟到”;然而,有些话要说,有点看法要与大家分享,因此不嫌“过时”。
本书原著法文,英译为Capti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般译为《二十一世纪(的)资本》或《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笔者以为都有商榷余地。“资本”为直译,虽意义暧昧,尚说得过去,译为《资本论》便有望题生义之误,因为此书最大的缺失为统计资料丰富而理论贫乏。因此,即使作者取书名时“心怀《资本论》”,且《经济学人》把他“誉”为“现代马克思”,有的报纸谈及此书时亦以“法兰西马克思”为题,但细心的读者应能看出皮克迪与马克思同调的只是看淡资本主义制度,如何矫正资本主义制度缺失的做法则完全相反。他虽然认为现行制度不公但不反对资本主义,而且相信通过连串社会、尤其是税务改革,便能拉近贫富两极的距离,进而达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和谐;与老马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搞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主张,南辕北辙。皮克迪“处理阶级矛盾”的手法固与马克思不同,《资本》的理论架构,以笔者的理解,亦嫌单薄,因此绝不能以“论”名之。
《资本》主要是论述二百五六十年来美国、英国、法国、瑞典和德国,旁及意大利、加拿大与日本的社会财富“钱落谁家”的问题。而他笔下的Capital,包括股票、债券、土地及现金,译为“财富”,似较“资本”更能达意。当然,皮克迪亦大谈二十一世纪政府应如何“重新分配财富”,以拉近贫富两极进而纾解社会的“深层次矛盾”。谈的均与过去、现在及未来的财富有关,笔者认为译成“财富”更合适(为了避免读者产生误解,本文提到此书,仍从众称之为《资本》)。
《资本》去年在法国出版,据作者提供的数据,卖出了约五万本。以法国未足七千万的人口看,销情不恶。其所以没引起“识字分子”热烈讨论,笔者的解读为:法国税率已高至接近皮克迪心目中的水平(高收入个人入息税率百分之八十),法国有钱人(“百分之一”)已深受高税之苦,因此社会上对向他们课重税的提议,反应冷淡。法国总统奥朗德于2012年5月上任后,很快把税率(绝大部分税项),尤其是物业税、遗产税、公司利得税及个人入息税大幅提高,法国巨(名气与体型)星、以演《大鼻子情人》为国人所熟知的德帕迪约,便因年收入百万欧元的税率突飙升至百分之七十五,而移民到单一税率百分之十三的俄罗斯(普京因此待他如上宾)。皮克迪对政治甚为热衷,且有把他的经济主张贯彻到政策中的志向,因此两度成为总统竞选人的经济政策顾问。他曾是奥朗德竞选团队的中坚分子(因此从任教的大学请假约半年),当前法国的高税率有他的“贡献”,几可肯定。
法文《资本》出版后,在法国固引不起公共知识分子和象牙塔蛋头的讨论热潮,英美更可说无人闻问(也许根本不知道有此书),直至英译本面世,才掀起轰动出版业、读书界,以至政坛的“书评狂潮”(至今尚未冷却;相信不少对传媒夸夸其谈的“评论家”只是拾人牙慧而未读原著):据出版商哈佛的消息,出版两个月精装版八万本便已售完(另加电子书一万二千多“本”),同数量的书料已陆续应市,创下了该社一百零一年历史的畅销纪录。
和大众化小说相比,这种销量微不足道,惟对非小说类尤其是早有“沉闷(忧郁)科学”之称的经济学书籍,有上万甚至十多万且可能突破二十万的销量,虽然多少与出版商安排皮克迪赴美“促销”,并获邀与财长杰克·卢(Jack Lew)会面交换对“财富平均化”的意见引起社会更广泛注意有关,但这种销售数字,确是十分惊人。顺便一提,在《资本》之前,“最”畅销的非小说类书籍为两位社会流行病学家合撰于2011年出版的《测量仪——何以愈平等社会愈进步》(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该书的英文本卖出约十五万册,创下新纪录。该书述说人人机会平等的重要性——美国多方面都不太“长进”,惟在机会均等上位居世界之首,而这是美国这个“负债王国”仍为世界最强(军事及经济)的一项根本原因,但过去少人注意!
《资本》译为英文卖得“美国纸贵”(英国版这个月才面世)且引起广泛讨论,清楚说明两个问题:一、书的内容必须“惊世骇俗”,有启发性建设性或危言耸听(因人而异);二、不管有多少人恶意贬低践踏,英文仍是当今世界(不仅仅限于自由)“识字分子”的共同文字,这等于英文媒介流传较广影响较大。当然,书的内容是否有新意是“热卖”的关键。以另一本去年英译出版的法文原著《平等的社会》(The Society of Equals)为例,虽然同样是以经济学原理及历史资料论述与《资本》相近的题材,出自同一译者Arthur Goldhammer之手,且同为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只因作者缺乏创意,没有提出令人另眼相看的论点,遂无法引起广泛讨论,遑论成为畅销书。无论如何,大家不得不同意,非英文著作国际影响力有限,译为英文才能“风行全球”,这是不容否认、不应忽视的事实!
《资本》“文本”五百七十七页,连注释及“引经”,共六百八十五页。内容如此“沉闷”、篇幅如斯冗长,非以研究贫富两极为专业的一般读者,恐难“终篇”。笔者因此有一提议,对经济问题特别是贫富不均现象有浓厚兴趣者,此书不可不读;兴趣一般非研究此问题的读者,读长凡三十五页的《导言》,知其梗概,便可“稍息”(如不读“文本”,五六页的《结论》亦不应错过)。此书的确值得放在书架方便处,以便随时取阅,因为除可读性高(也许与译笔流畅有关)的《导言》外,其涵盖过去两百五六十年欧美多国的经济特别是统计财富的数据,是不可错过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大都绘制成或编列为一目了然的图表或列表,方便读者查阅。不过,“多如牛毛”的数据中,若干数据的真实性、可信性已引起论者质疑,伦敦《金融时报》(FT)甚且以头版头条新闻形式报道其经济事务编辑贾尔斯(C. Giles)的有关论述,可见此中确有一些问题。然而,皮克迪在书中一再指出,由于不少数据并非来自“政府统计处”(当年尚无收集统计的意念,当然没有有关机构的设立),因此不是“绝对准确”,却肯定可看到当年的一般情况,用作参考,并无害处。正因为如此,遂有人指出,对书中某些数据的诸多挑剔,也许是皮克迪暴得大名引致“职业性妒忌”有以致之。克鲁格曼对此亦大不以为然,6月1日在他的《纽约时报》专栏说得更妙:“I'm not accusing Mr. Giles of being a hired gun for the plutocracy.”——这位诺奖得主究竟想说什么?“你懂的!”事实上,本书搜集的数据不是那么不济——皮克迪与数名同行多年搜证搜集整理而成的数据,在笔者看来,即使偶有疏漏,亦十分珍贵,且极之实用!
《资本》出英文版之前,皮克迪在法国,肯定不如今日在欧美那般家喻户晓。从他的简历看,你可以说他是神童,但说他早慧及少年得“意”,似更准确——1993年他二十二岁便获“伦敦经济学院(LSE)”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其论文正是研究“财富再分配”),同年受聘为美国麻省理工(MIT)经济学系助理教授,至1995年辞职,加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为研究员(他认为在祖国工作更能发挥所长);2003年出任由他主催成立的“巴黎经济学院”教授,且于2006年被委任为校长。但他上任不久,便为出任当时竞选总统的社会主义健者Segolene Royal(现政府的生态、持续发展及能源部部长)的经济顾问而辞“官”,2007年起回校担任教授兼任法国社科高级学院(EHESS)总监至今。
2001年,皮克迪出版一本分析百年来(从1901年至2001年)法国高入息变化的书,引起研究相关命题学者的兴趣。牛津学者艾京逊(A. Atkinson)和在加州柏克莱任教、与他合作研究相关问题多年的法国学者赛伊(Emmanuel Saez),分别搜集美国及欧洲数发达国家的有关数据,年期远至十八世纪,由于成绩甚佳,结果他们成立了“世界高入息数据库”(The 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 WTID)。掌握了庞大数据库的统计数据,终于成就了《资本》这本轰动学界政坛、毁誉交加的专著。
应该指出的是,《资本》所援引的数据,绝大部分是从地方政府以至商会之类的民间组织及教堂档案翻查而得,颇费工夫却不免疏漏;由于资料来源多元,搜集的方法并不统一。这些瑕疵都为学者专家所诟病。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叶,“先进”国家政府相继进行“户口调查”,有此现成统计,省却了皮克迪和他的合作者许多麻烦,可是,他们却认为政府的统计只集中在低下及中间入息家庭,大有不足。事实上,政府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这类收入阶层,适足以反映社会上大部分人的经济状况,因此非常有用。可是,对目的在研究收入不均、贫富两极的学者来说,他们最需要的高收入家庭的相关统计却付诸阙如,这意味着缺乏比较贫富两极家庭经济情况的资料。
为了弥补此一缺失,皮克迪和他的合作者只好自己动手,他们设法取得法国和美国“百分之一”家庭的报税表,对照之下,“百分之一”(遑论“百分之零点一”)的收入与低中阶层的入息差距愈拉愈阔……皮克迪的发现,彰显了2011年9月至10月美国“各界人士”占领华尔街并向全球发出拉近贫富悬殊呼喊的公义性!
笔者“滞后”写本文的一项“优势”,是有机会拜读皮克迪对指摘他的统计资料及“方法论”(所用以比较相关数据的方法)有毛病的回应。5月30日,《纽约时报》据皮克迪贴在其个人网站上的四千多字、反驳《金融时报》大张旗鼓“指控”他种种疏漏甚至错误的长文,笔者以为他的辩解不无道理,可以接受,反而是《金融时报》的论点有不少是吹毛求疵甚至是无的放矢。举个简单例子,关于英国的“财富不均”,皮克迪用的是“税收单据”的数据,得出“百分之十”有钱家庭拥有全英百分之七十一财富;《金融时报》据“全国性调查”的资料,同一批人只拥有全国百分之四十四财富……究竟哪种数据较可靠?非常明显,皮克迪所用的数据较贴近现实,因为富裕阶级倾向以不尽不实的数据填写调查表格(即使是政府统计部门的调查),“少报”对他们并无害处,“如实道来”却可能不利,因他们的收入也许“太多”,而这会惹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比如当局可能调查这些庞大资金是否由非法途径如逃税漏税以至做非法生意所得,他们的“自报”因此不可靠!向政府隐蔽财富(“报细数”)是富裕阶级的传统,在私人场合“炫富”是另一回事。
《金融时报》的批评,当然有一些大有道理且为笔者认同,比方说,皮克迪只有英国、法国及瑞典的资料,便说成是欧洲的情况,这当然不周全。此外,若干统计,皮克迪未予“加权”(weighted)处理,确是疏忽。但这类小错不致影响《资本》的主题——社会财富不均的情况有回复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严重“复古”情况!皮克迪用了不少篇幅论述何以他在《资本》中展示的数据可信性较高,最后反问,如果《金融时报》的说法正确,那么,英国便是“历史上财富分配最平均的国家”。这有可能吗?答案显然已写在墙上。
皮克迪指出,在发达(已开发)国家,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一”)手上,他们赚钱(聚财)能力这么高,皆因拥有资本(Capital),因此有利息、租金、股息、专利费以至资本增值等收益,更重要的是在漫长的两三百年间,“资本”的回报率大部分时间都高于经济增长率,那等于说坐拥“资本”者的收入,“注定”高于出卖脑力和劳力的人!这种情况较明显的国家,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是法国(尤其是)意大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期间,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较为缓慢,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远远落后于“以钱生钱”(用皮克迪的话“Money tends to reproduce itself”)的营生,当年的法、意遂做不成富裕大国。
皮克迪搜集的多国数据显示,在十九世纪,租金(主要是耕地)年回报在百分之四至五,二十世纪的租金(住宅、工商物业以至耕地)的收益率亦在同一水平;债券孳息从十九世纪至今,大多时间徘徊在三至五厘;而证券年收益(股息加股价未除税)大概超不出百分之七至八的范畴……
他因此判断在那两三百年,“资本”回报的平均数在百分之五(五厘息)前后。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明显较为和缓,入息与经济挂钩者便远逊。《资本》的统计显示,在1700年至2012年这三百余年间,全球的人均国民毛产值平均年增幅百分之零点八;虽然工业革命成功及人口结构的变化,令二十世纪的人均GDP有较为可观的增长,但长期趋势向下,十分明显,比如1950年至1970年经济平均年增长百分之四,1990年至2012年已降至百分之三点五。看当前的国际经济发展形势(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如树懒爬树,费尽气力才有“分”进),他预期2030年至2050年有关增幅跌至百分之三,而2050年至2100年更可能只有百分之一点五(经济放缓的根本原因为科技不易再有突破)。
从上述两组数字看,经济增长的收益远逊“资本”回报,是谁都看得出来的。以《资本》的理论架构,皮克迪因此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制造了社会财富两极化,换句话说,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与一地一国的经济政策关系不大。
皮克迪为“手上财富”即资本年回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定下一个“程序”,前者以r标示,后者则以g为号。这个r代表“资本”产生的利润、股息、利息、租金及其他衍生收入,g则是经济增长带来的年收入或经济产量。“资本”收益长期大于经济收益(他的推算为五比一强),r > g(“资本”收益大于经济收益)遂成为贯穿全书的主题。在现行社会制度尤其是税制不变的前提下,广义的有钱人(有余资收息及收租的所谓“食利者”〔rentier〕)便“富者愈富”,穷人未必愈穷,惟穷人收入增幅远远追不上富人入息的增幅,结果贫富差距愈来愈大,令有心人担忧资本主义社会可能因贫富两极越走越远而阶级矛盾恶化,酿成社会“不和谐”,这正是皮克迪绞尽心力要把两极拉近的原因。
资本回报大于经济收入的r > g令资本主义制度可能面临重大冲击,有利于财富累积“富者愈富”的时代带来社会不公平,而助长这种现象形成的另一项重要元素是“长嗣继承”。这是大部分国家行之有年的传统,可说自父系社会确立以来即有。因为“古时候”土地是主要财产,土地若不断分割分给子孙,不出八代十代,一个大地主便变为无数小地主,等于大富之家变为无数中产家庭。那当然是深明大富家族有政经优势的族长不愿见到的发展。在上层社会(aristocratic societies),这种情况尤为显著。也就是说,只有长子嫡孙才能继承家族(全部或大部分)财富,也是贵胄阀阅之家保持世代财雄势大显赫家风的有效安排。我国(包括大部分香港豪富)传统上的各房子孙在族长谢世后按辈份分家产,这在欧洲特别是英国并不流行。
在继承家财上有绝对优先权的长子嫡孙,他们对家族唯一“应尽的义务”,是必须想尽办法保住这笔家产,使其不致萎缩同时凭其收益(利息或租金)便能过如父辈般的好日子。而他们“应尽的任务”,则是把这笔原封不动或有所增加的财富传给下一代……这种代代相传等于上代无偿送给下代的“制度”(entails),在不少国家(尤其是英国)迄今未衰。皮克迪在本书第三卷“结构性不均”中举了不少“小说家言”,以说明这种制度早已存在,如大家熟知的英国作家简·奥斯丁及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的小说(前者的《理智与情感》《曼斯菲尔德庄园》和《劝导》及后者的《高老头》),对此均有生动深刻、具体而微的描述。在这些小说中,收入(income)指的不是薪酬(即不是凭劳力脑力获取的收入)而是家族产业(如耕地)的租金(亦称不劳而获的财富)。这种现象不仅见诸英国维多利亚、爱华德与法国拿破仑时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诸国都是如此……
欧洲封建王朝对贵族家产的保护,读者不大熟悉的法国似乎最“离谱”。皮克迪指出法国大革命(1789-1799年)后,法国政府负债累累的一项主因,是“赔偿财主在大革命中的财物损失”。当暴乱发生时,地主阶级逃离家园避难,不少佃农、农奴弃铲而起,成为暴民,打家劫舍固不待言,他们的“脱产”还导致庄园被毁、财物被盗、土地失收,这本是大革命必然导致的人祸。但拿破仑三世政府在贵胄地主的联合压力下,竟然对他们作出“以十亿法郎计”的赔偿,借以换取他们的政治支持(可算是最典型的皇贵〔官商]勾结),当年国库空空如也,政府只有高息举债……《资本》并未列出具体数字,只说单是赔偿金额的利息支出便约为当年国家收入(其时尚无GDP)百分之二!在这段时期,皮克迪根据“遗嘱文件”的统计,显示巴黎属“富裕阶级”的人数从大革命刚过的1800-1810年有百分之十五骤增至1840-1850年的百分之三十。这些人占有全国百分之五十至九十的财富!
和法国一样,大部分西方国家的财富分配都循r > g的程序运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性经济萧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高税率、高通货膨胀率和战火摧毁了大量财富,意味着不少富裕阶级有巨大损耗,有的甚至倾家荡产(民智渐开、政治制度民主化,财主已失去拿破仑三世时期向政府“索偿”的可能)。战后特别是二战后,美国勃兴、欧洲重建以至日本崛起,带动全球大部分国家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平均收入大增(当然有资本家希望工人成为其产品消费者的深意而给他们加薪),加上二战后心智开明倾向保护受薪阶级权益(最明显的是工会势力大盛)的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思想,纷纷进行税务改革、实施这样那样的福利,这种发展对富裕阶级不利,不在话下。财产损失及高税负,令战后至八十年代初叶约三四十年间,“资本”收益增幅逊于经济增长的收益,那等于财富不均情况稍有改善。
这种现象,正是有“国民所得之父”之称顾志耐(Simon Kuznets,1901-1985;七十年代初期笔者译其名著《现代经济成长》[Modern Economic Growth-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时用库茨内斯的译名,他于1982年获诺奖时,台湾学人译之为顾志耐,极佳,遂贪新忘旧)将之“归纳”为“颠倒U形曲线”(Invented U curve亦称Kuznets curve,其图像与“拉发曲线”相近)。顾志耐认为从1913年至1948年间,美国贫富的差距大幅收窄,统计数据显示百分之十的富裕阶级所拥有的国民收入,从占百分之四十五至五十下降为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初期,得益的只限于高收入阶层(如工厂东主、决策层及地主),受薪者所得有限(仅堪温饱);经济持续上升,水涨船高,全民(指就业人口)随之分享较多经济成果,结果拉近了贫富的分际(以图像示之有如颠倒U字)。顾志耐的看法正确,却嫌不全面及缺乏“历史感”,皮克迪的分析相较之下更为深入,他指出期内贫富差距缩窄的主因是经历二次世界大战和一场古之所无今仍未见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
无论如何,在这期间,经济蓬勃发展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就业市场供不应求,工会也为工人力争,加上有或多或少的“免费午餐”,令受薪者分享了经济蛋糕的较大一份。非常明显,这是受薪阶级物质生活改善最快的日子,人们不但温饱无忧,拥有现代化的家庭电器用品,电视机吸尘机洗碗机空调机一应俱全,汽车从奢侈品降级为家家供得起的日常必需品,而且有了更多的闲暇“享乐”(服务业因而蓬勃起来),自置物业热潮亦由此而起——自置物业,成为有产阶级,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直至二战前,是受薪者想亦不敢想的“豪举”,也就是说,在那段时间,置业是受薪者的“妄想”!
可是,分享经济成果的受薪阶级好景不常,因为八十年代初期以降,各“先进国家”经济增长均大幅放缓,等于“以钱生钱”者的收入,再次大大超过入息与经济增长挂钩的受薪者,这就意味着后者的实质(撇除通胀)收入倒退,《资本》中列举了很多早已见诸媒介、为读者熟知的具体数字,这里不引述了。皮克迪看到的景况是,过去二三十年身家骤增的有钱人,包括财富世代相传的早富之家(Old Money),从科技创新赚大钱的才俊到占尽市场及小股东便宜同时以攻守同盟瞒骗政府大钻法律空隙逃税瞒税的金融市场(美国华尔街、英国金融城和中国香港中环)大鳄(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自我审定的花红、认股权及坐盘买卖等,因此不能视之为“受薪阶级”),其财富堪称天文数字;他们的后代,不论是受惠于欧洲的“长嗣继承”或受益于亚洲的“各房平分(实际上当然是内外亲疏有别)”,都成为坐拥庞大“资本”而且财富大幅——比起经济增长——增加的豪富。
由于这类富二代或二世祖举目皆是,就意味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社会财富两极严重化程度日甚一日。如今世界经济不是在增长与衰退边缘挣扎,便是踏步呆滞不前(中国与印度皆然),以资本赚钱的投资/投机市场则兴旺胜昔,拥有巨资的人,只要坐收利息(当然不是欧元的负利率而是基金经理为客户量身定做的有五六厘年息的投资组合),便财源广进,财富不断累积。复利的神奇功能令财富于无声处有序、快速地大幅增长,拉阔挖深了贫富之间的鸿沟。约二十五年前,笔者曾不厌其烦详细介绍“七二法测”(Rule of 72),即利息除此七十二,所得之数,便是资金“翻一番”所需年数(这是统计演绎并非数学公式,因此并不绝对精确)。这种现象正是导致近年来世界各地的阶级矛盾日益恶化、社会因而日趋“不和谐”的一项不容忽视的因素。
富二代借复利滚存累积财富,《资本》以读者应该熟悉的法国化妆品欧莱雅的继承人李莉·贝藤阁(L. Bettencourt及美国超市沃尔玛的子孙)为例,在1990年至2010年二十年间,微软创办人盖茨的身家由四十亿美元增至五百亿,贝藤阁则由二十亿美元升至二百五十亿(平均实质年增幅均在百分之十至十一之间)。盖茨是创新企业家的典范,财有应得;贝藤阁终生未工作过一秒钟,凭祖荫便富可敌国,正是这类过去三十多年西方社会“诞生”数以十万计不劳而大有所获的巨富,令贫富两极化愈来愈厉害!
如何纾解贫富两极的不公平现象,为了避免流血革命,皮克迪提议可考虑从征收高税上着手,比如大幅提高入息税、利得税、物业(土地)交易税以至资本增值税,特别是遗产更要“重税伺候”。但这类针对富裕阶层的累进税都会带来深度的消极影响,个人和法人都会请世界一流脑袋(税务律师和会计师)为他们设计合法的避税方法,加税的结果反令政府税入萎缩。有钱人避税自肥之外,还会早早将财富馈赠后代亲朋以逃过高税关,更会向低税免税地移民和迁册,到头来政府反可能得不偿失。
皮克迪当然了解有钱人为“保障私有财富”无所不用其极,因此他指出各国应“有商有量”,然后征收统一“环球财富税”,这确是阻遏“财产世袭资本主义”(Patrimonial Capitalism)的深化、纾缓财富两极的良方。但这可行吗?答案是绝不可行。因为在这个各国“互相博弈”(似为当今评论界的“潮语”)的世界,必然有些国家如英国、瑞士、卢森堡、新加坡,或地区如香港甚至上海,我行我素、众加独减,不理会、不加入此类“税务联盟”以吸引“热钱”流入。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与有钱人为善”的国家或地区,必然成为世界“热钱”的集中地,这意味着外资源源流入。
有点不可思议的是,皮克迪和数十位评论《资本》的学者及传媒人,都未提“杜宾税”(Tobin Tax)。参与股市游戏的读者,应听闻过“杜宾的Q”(《资本》亦有提及),也知道这位诺奖得主于1972年曾有环球抽取外汇投机税(每宗外汇买卖都抽一点点比如交易额百分之零点五的税)的建议,这种后来被称为“杜宾税”的税项一旦环球贯彻,当可稍戟外汇投机之风、令外汇市场波幅收窄。但谁有号令各国都行此税的权力?答案是没有。此法虽是抑制外汇炒风之妙法,却因此不了了之。“环球财富税”亦将同一命运!
要怎样评价皮克迪的《资本》,现行制度的拥护者维护者亦即是保守派(笼统的“右派”),对之抨击不遗余力,可以理解。他们的论说,简略而言,可以八十年代一度成为“显学”的“拉发曲线”概括之——税率“太高”不仅会打击工作、创新意欲,还会导致资金人才双双流失,高税因此反会使政府税入下降。因此,现在优惠资本阶级的政策不宜变。中产和低下阶层若有不满,抛出几块带肉骨头(有限度的免费午餐)便可“定风波”。另一方面,眼见贫富鸿沟太阔太深令“社会深层矛盾”随时爆发成社会冲突(占领华尔街不过是“药引”而已),鼓吹改革现行制度的“公共知识分子”愈来愈多,他们担心若不设法改变现状以拉近贫富差距,社会动乱甚至出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都有可能。在这种人心思危的气氛下,皮克迪力主向富裕阶层特别是“世袭财富”开刀,便获广泛支持。当然,主张抽取“环球财富税”是断对症但下药太霸道,非常难行甚至不可行。
作为一部普及性学术著作,《资本》确有若干错漏,5月12日徐家健教授在香港《信报》的文章指出皮克迪完全忽视贝加首创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而在《金融时报》之前,大名家费尔斯坦(M. Feldstein)已在5月15日《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皮克迪有资料不完备便遽下结果的缺失。这些批评都是有道理的。不过,皮克迪强调的r > g,三十多年前已如此,于今愈演愈烈,对有心拉近贫富差距(不是对“穷人”特别关顾,只因问题不妥善处理,社会必然日趋混乱以至危害资本家利益)的政客、学人和论者,这是一条明确的研究新路向。换句话说,从今而后,最终目标在拉近贫富距离的经济政策,最好是以“劫富济贫”定调。
香港是个贫富差距极大的国际都会,这是港英政府的政策长期向富裕阶级特别是物业发展商倾斜的结果。这种政策在回归后持续,造成“港亿万豪门比例冠全球”的事实。据于业界享盛誉的美国波士顿顾问集团(BCG)6月10日发表的报告,在2013年,香港每十万户有十六点六个“起码坐拥一亿美元”的家庭,比例全世界最多(参考资料:瑞士第二、奥地利第三、挪威老四、新加坡第五……美国第十);而财富超过百万美元的家庭,香港全球排名第十一(参考资料:美国第一、中国内地第二、日本第三)。这显示“富者愈富”在香港的“严重性”。不难想象,香港“百分之一”与平民百姓的财富真有天壤之别。面对这种现象,特区政府,尤其是早非公务员而具政治任命身份的财政司司长,当然得动动脑筋,在坚持稳健理财“哲学”的同时,应该加入一点新思维,比如恢复征收遗产税、红酒税及行累进入息税制……连亚洲首富、长江实业主席李嘉诚亦与世界首富“包发达”一样,主动提出应加点税,政府又怎能抱残守缺……量入为出绝对正确,但税入若增加,“量出”便较可观,这种可令更多人受惠且可纾社会怨气的政策,当局又何乐而不为!?
皮克迪是三个女儿(最大的十八岁)的父亲,看似“宅男”(不是不离家而是不离国),从2000至2001年任麻省理工的访问教授后,除了赴外开会或如这趟去美国为本书促销,他几乎足不出国门。他写了不少学术著作,同时是法国《世界报》及《解放报》(Liberation)定期、不定期的专栏作家,所写当然环绕贫富两极的成因及财富分配……读(或浏览)过《资本》的人,都会为皮克迪仔细分析那些涵盖面极广的统计(他对过往众多经济学家收集而不分析这些历史性统计感到意外),肃然起敬。本书篇幅甚长,也许与他不屑用计量经济学程序剖析问题有关,所以如此,大概是为了照顾一般读者,也可能是这位数学学士出身的学人根本就认为抽象数理程序无法解决现实问题。事实上,他对计量经济学确无好感,他调侃地指出,计量经济学家“对数学有天真幼稚的激情”。虽然计量经济学已失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光环,这种看法却肯定得罪了不少仍居学术殿堂高位的经济学家!
本文作者林行止,文载2014年6月22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