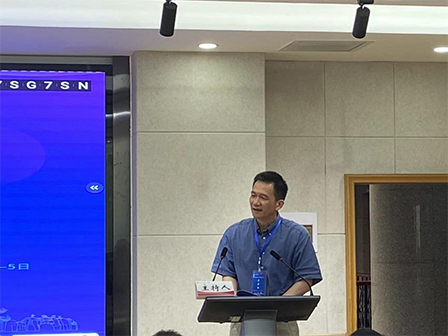地权:虚实之间的尴尬
书刊 · 2011-03-10 00:00
返回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1980年代初论及大陆由乡入城的改革时曾断言,国企改革将不如农村改革那样顺遂,因为当时视“股份制改革”为畏途的国企,将面临产权虚置的难题,而农村改革能够回避这个问题。因为土地易于分割,可以轻松量化给农户,...
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1980年代初论及大陆由乡入城的改革时曾断言,国企改革将不如农村改革那样顺遂,因为当时视“股份制改革”为畏途的国企,将面临产权虚置的难题,而农村改革能够回避这个问题。因为土地易于分割,可以轻松量化给农户,辅之以数十年的承包权,几乎可以视同为“所有权”,如此一来,产权激励的问题暂时得到解决。
国有企业的厂房、设备、生产资料等动产或不动产,则无法轻易切割,在股份制未实行的情形下,只能一股脑打包给承包者。“无恒产者无恒心”,国企承包者中普遍出现了短期行为,置设备维修和长期投资于不顾,更遑论技术研发。于是,1990年代初,国企承包纷纷被叫停——产权终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
这就有了1996年,《经济日报》社原社长艾丰写下名噪一时的《改到深处是产权》一文,产权改革之“深水区”性质由此可见一斑。
如今,因可以暂时虚置而绕行产权难关的农村地权制度,也走到一个尴尬的关口:面对咄咄逼人的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的产业化,原本被视作制度创新的“准产权”,显得脆弱不堪——面对“国家”的征地,“集体”几乎毫无议价能力;面对资本的下乡,由村干部具象化的“集体”又往往罔顾村民利益而有私相授受之嫌。因此,国有和集体土地的同市同权任重道远。
如何“细分、实施和保护”地权,便成为中国当下一个重中之重的命题,而张曙光《博弈:地权的细分、实施和保护》一书,正是通过条分缕析的阐释及详尽的案例调查,为寻找解决地权“死结”的变通之道,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和解析框架。 细读此书,人们既会为现有土地制度安排中的刚性缺陷而扼腕,又会对各利益群体善于发现“弹性空间”进而“合理变通”会心一笑。由于农村地权集体所有,无法“私有化”给个人,许多事关权益的文章便只能围绕“用益物权”来做,因此便衍生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等诸多名目的权属,而这不同的“权”,又面临不同的流转范围,所以同为“农地入市”,其“地”其“市”之不同,足以令外行人产生雾里看花之感。
原则上说,宅基地使用权所入之“市”最为狭窄,基本不出村,出村也不出乡;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越乡跨县,但若想从此“市”入彼“市”——从“农地”之“市”转进“非农地”之“市”,则难上加难,虽然各地不乏以农业产业园的名目暗渡陈仓的案例。眼下比较瞩目的是集体建设用地的“入市”,此“市场”对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以满足乡村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用地需求,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间的利益分配公平与否,则端视主导“入市”进程的是村干部,还是村民集体组织。
而最拨动各方心弦的则是集体建设用地如何进入“城市”,此一“入市”所产生的巨额级差地租是各方不遗余力争夺的,其间涉及到的“国家”与“集体”之争,“国家”内部的中央保“18亿亩红线”与地方要发展之争,“集体”内部的干部与村民之争,”“国家”“集体”与体现为用地企业的“市场”之争,错综复杂,远胜春秋战国时期之合纵连横。
因此,土改,正在过大关。这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土地“战争”的走向,将决定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进退成败,面对这纷纭复杂且快速演进的现实,犬儒主义的“一切皆有可能”是有害无益的中庸,只有各利益群体理性公平“博弈”下的各方利益最大化,才是最值得努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