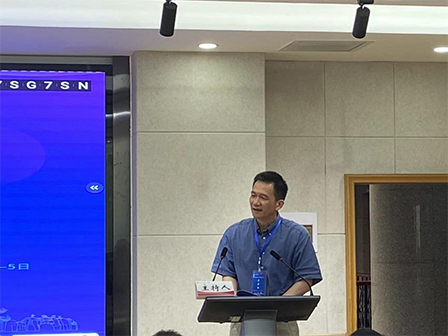《幸福经济学》:你不能度过一生,却没有见到生活
书刊 · 2010-06-07 00:00
返回摘要:对中国人来说,发展有一种特殊的意味,在它之前,是饥饿、贫困,需要的是就业和饭碗,没有什么可以高于这个目标。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不管它是不是有污染、是不是低工资,在推动者来说,都是发展。人们惊醒之时才发现,...
摘要:对中国人来说,发展有一种特殊的意味,在它之前,是饥饿、贫困,需要的是就业和饭碗,没有什么可以高于这个目标。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不管它是不是有污染、是不是低工资,在推动者来说,都是发展。人们惊醒之时才发现,所谓的发展已经按照自己的逻辑,造就了城市停车场、令人沮丧的高房价、餐桌上靠激素催大的鸡鸭鱼肉。

《幸福经济学———创造真实财富》,(加拿大)马克·安尼尔斯基著,林琼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2月版,49.00元。

《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瑞士)布伦诺·S·弗雷、阿洛伊斯·斯塔特勒著,静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32.00元。
对于幸福的反思并非始于今日。从几年前种种关于城市幸福指数的话题开始,人们得了一种关于“幸福”的相思病,人们渴望幸福、渴望做回自己,但之所以格外渴望的原因仅仅在于一些简单的人之为人的需求离我们如此遥远,以至于我们多数时候仅仅称得上生存,而不是生活。
在住上城市高楼、拥有私家小车、物欲不断满足之后,人们开始怀念乡间小路,野菜——— 也许还是产在大棚———成了高档餐厅的佳肴,农家体验、原野采摘正成为时尚……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城市已经变得越来越远离生活本身。而这离当初只想有饱饭吃、做城里人的梦想才不过30年。这个世界奇特得像一面魔幻镜,让人们无所适从。当然,让人们陷入恐慌的不只是这些,它的背后是以发展的名义带来的污染,被疏离的人际关系,把家当成过夜旅馆的工作机器,上了发条一样的奔波。
对中国人来说,发展有一种特殊的意味,在它之前,是饥饿、贫困,需要的是就业和饭碗,没有什么可以高于这个目标。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不管它是不是有污染、是不是低工资,在推动者来说,都是发展。人们惊醒之时才发现,所谓的发展已经按照自己的逻辑,造就了城市停车场、令人沮丧的高房价、餐桌上靠激素催大的鸡鸭鱼肉。
这是在城市。在农村,人们也在被迫卷入这场无法拒绝的豪赌。今年4月,一次长时间的南方出差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日渐富裕的乡村,我感到陌生而吃惊。农民的房子越来越大,但不再有袅袅炊烟,不再有家长里短甚至妇人骂街,不再有孩子们嬉笑打闹,儿时所见的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已经不见踪影。新修的房子,装饰得气派而显眼。可房子修好却大都空置,它的主人们都外出打工,常年住在地下室或者工棚。长期两地分离,为人父母的没法照顾小孩,下一代的教育就成了大问题。青壮年出门打工,老人们带着孩子,管不住,一些不听话的孩子就结伴出去混———结局很简单,只要不读书,他们就是农民工第二代、第三代。但即便如此,这些农村的主力军仍然大年一过就往城里跑,在城里才能挣到让自己相对富裕的金钱。在金钱维系的生存中,他们别无选择。
在迅速逃离了饥饿与物质奇缺的折磨之后,城市与农村都陷入了生存的恐惧之中,人们无法确认今天的自己是否真的比30年前的自己更加幸福,或者可以说,经济的发展反倒使多数人远离幸福,“蜗居”、“剩女”的存在或是注脚。我所描述的城市与乡村残酷,对于更多的人们来说都有着或多或少的感受,尽管我无法用更理性的分析将此种铺天盖地而来的“恐惧”更清晰地描述出来。
在这方面,《幸福经济学———创造真实财富》一书做了令人惊喜的努力,尤为难得的是,作者将这种关系的描述置于国家经济政策与走向的大背景之下。作者对包括更长的寿命、整体社会福利、青少年健康状况、更多闲暇时间以及与家人、朋友的共处等28项指标进行研究的数据显示,与1950年相比,美国公民现状恶化的指标达到20项,仅有更长的寿命与繁荣的经济等7项指标有好转,其中贫困率不变。而在另一项对加拿大艾伯特省经济、社会、人力和环境资本的统计中,可以看到,在1961至1999年中,人们无偿工作小时数增加了4%,其所创造的价值相当于326亿美元,或G D P的31%;父母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减少了33%,家庭破裂比率(离婚与分居)上升了312%;交通事故增长了37%;人均犯罪率增加了59%……更不要说湿地的减少与河流的污染。马克·安尼尔斯基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展示了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人们所遭遇的“发展”困境,尽管他的分析模本是大洋彼岸的发达国家。我们说不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子,可我们正在一如既往地重蹈覆辙。
对中国来说,它同时有着另一重要的价值:于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与主导者而言,如何改变单纯“数字”的增长与不计后果的工业化,以及与此带来的贫富差距、社会分配不公、环境的极度破坏,这本书提供了最为简洁明朗的警醒。
当然,对于个人,怎样认识财富,在金钱面前如何坚守基本的生活原则,也是很必要的。在这个方面,《幸福经济学》同样提供了有益的思路,通过对“个人真实财富评价”机制的引入,从一个人的教养、社会活动与人际关系、锻炼身体、有意义的工作、生存环境、收入与物质财富等多种角度,展现了幸福的基本构成———而在过去三十年,我们中国人过于追逐金钱,牺牲的正是对精神的追求、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至身体本身。当然还包括审美情趣的庸俗化、大众阅读的缺失与低格调趋势,对教养本身的忽略。
作者并不诅咒金钱,他用“光芒依旧的货币”描述自己的信心,尽管“该死的金钱”以及让人们批评的物欲横流与利欲熏心种种,背后就是“该死的市场经济”本身。但不要忘了,经济学本身并非肆无忌惮如斯,古典经济学终伴随着伦理学的拷问,伟大的亚当·斯密在其不朽经济学著作《国富论》推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同时,在《道德情操论》中描述了他的敬畏:“出于挂念自己的福祉,我们会具有审慎的美德;出于挂念别人的福祉,我们会具有正义和仁慈的美德。审慎约束我们免遭各种伤害,正义和仁慈则促使我们关注他人的幸福。”在他看来,道德和正义对于一个以市场驱动的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如此看来,我们今天面临的真正困境是,政策主导者和大众怎样反思自身逐利过程中的道德放逐与基本原则的节节败退。安德烈·纪德说,我们不能“度过一生,却没有见到生活”。《幸福经济学》或提供了这样一种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