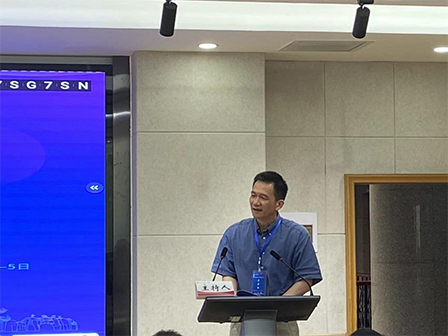增长模式转换何以知易行难
书刊 · 2005-02-11 00:00
返回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单纯依靠提高投资率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基本走到尽头。这种模式所能产生的增长潜力即使尚未枯竭,也已是强弩之末;如果不能及时改变,增长的放慢将不可避免。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比值)...
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单纯依靠提高投资率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基本走到尽头。这种模式所能产生的增长潜力即使尚未枯竭,也已是强弩之末;如果不能及时改变,增长的放慢将不可避免。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比值)呈直线上升趋势,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25%左右提高到2003年创记录的40%以上。据国家统计局初步统计,2004年GDP约为13.6万亿元,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7万亿元!在此期间,GDP的增长围绕着10%的水平波动。换句话说,中国维持这一增长速度,所依靠的不仅是高投资率,还必须不断提高投资率。
然而,单纯依赖投资的增长是有极限的。投资率在理论上不可能超过100%,从中国和国际上的经验看,实际的上限似乎在40%左右。有人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还可以持续20年,那么如果根据历史数据进行外推,这意味着投资率要超过50%。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经济可以承受如此之高的投资率。
以日本为例。在其战后的重建中,投资率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20%上升至70年代的大约35%;随后,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进入了下降通道,由35%的高位滑落到2003年的25%。韩国大致经历了同样的周期,投资率在高峰时接近40%,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即开始下降,近几年保持在30%的水平上。
国际经验证明,单纯依靠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不具备可持续性,投资率或迟或早总要降下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投资率远远低于亚洲国家,如美国的投资率常年稳定在15%左右。显见,可持续增长靠的不是投资,而是技术进步。
针对传统增长模式的问题,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大力推进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不应单纯地追求数量,而要重视增长的质量;要从追求速度转变为追求效益;要从依靠资源投入,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要从生产能力的投资,转变为研发投资。新增长模式的要义是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而不是资源使用数量的增加。
尽管历届政府无一不强调转变增长模式的重要性,甚至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有关于“外延式”和“内涵式”增长的讨论,但投资率始终不断上升,经济增长模式仍然是外延式扩张;“大干快上”的热潮不仅没有降温迹象,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
新增长模式的难产反映了传统模式的顽固,而传统模式的经久不衰,又在于它深厚的制度根基。只要这个制度基础存在一天,中国经济就摆脱不了单纯追求速度的取向,就只能是拼投资,拼资源消耗,增长模式的转变也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传统增长模式制度基础的核心是政府主导资源的配置,特别是生产要素如土地、人才和资金的配置。作为非赢利机构,政府配置资源不可能也不应该以利润或者效率最大化为目标,政府自身的激励机制决定了它追求的是规模和速度。由于经济的表现往往是政绩中的最重要一项,各级政府无不以GDP增长为硬指标。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对规模的偏好,还来自于规模与个人利益的关系:规模越大,个人可以支配的资源就越多,而可支配资源越多,个人的隐形收入就越高。正因为这些原因,国际上曾有经济学家总结为:“私人企业最大化利润,公共部门最大化预算。”后者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铺摊子、上项目。
政府对社会投资活动的决定性影响表现在投资周期与政府换届的重合上。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在扣除物价因素后达35%,为改革开放时期的最高值。投资在五年后即1998年出现另一小高潮,实际增长为14%,而在相邻的1997和1999年中仅有7%和6%;再过五年,固定资产投资于2003年实际增长为26%。近年来,国有部门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估计在40%到45%之间,实际上通过项目审批、土地和信贷等政策,政府在投资领域中的作用远远超过这一比重。
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另一制度基础是要素价格的管制,土地和资金的虚假低成本鼓励了过度投资和忽视效益的倾向。各种各样的“开发区”、“首长项目”、“面子工程”可以拿到廉价的土地,资金成本也被人为扭曲。由于个人投资渠道狭窄,储蓄资金流入以国有机构为主体的金融系统,储蓄者不得不接受官定的低利率,不得不面对资本市场上限制股票供给所形成的高价格和低回报。廉价资金支持下企业的盲目扩张,在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都发生过,其不良后果也早已为人们所熟知。
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的薄弱导致中国企业短期扩张的强烈冲动,而长期投资尤其是研发投资明显不足。新产品、新技术发明不久就被仿造,低价伪冒品泛滥,企业无法回收研发投资,因此失去创新的动力。中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也制约了研发的开展,从事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的企业得不到风险基金和创业基金的支持,这些基金至今既无法律地位,又因法人股的不流通而丧失了主要的退出渠道。
认清了传统增长模式的制度基础,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需要逐步退出投资和融资领域。在投资主体方面,要降低国有企业在商业性投资中的比重;除了公用事业,政府不再作为投资项目的策划人、发起人、融资者和负责人。至于投资立项,政府应只管环保、安全等社会指标,取消其它所有形式的行政审批和市场准入限制。
就融资体系中的改革而言,需要解除对资金价格的管制,推动利率市场化,继续提高基准利率;停止对股市的政策干预,改变股本资金成本实际近乎于零的不正常现象。让市场决定价格,让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抑制过度投资。金融机构改革的重点无疑是银行,银行要成为以赢利为目标的、独立的金融企业,根据投资项目的风险和收益而不是政府的意图发放贷款,由此形成对政府或者企业扩张冲动的有效制约。此外,还需要抓紧进行风险、创业等股本投资基金的立法,并尽快实现法人股的流通,创造退出渠道。
铲除传统增长模式不断复制的制度基础,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退出经济、退出市场,集中精力推动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惟有如此,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