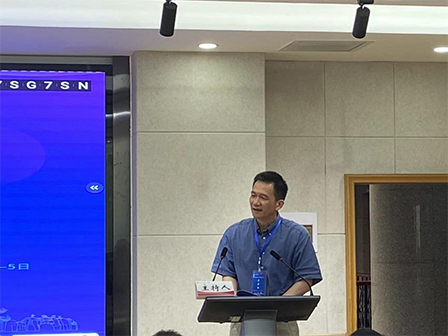中国证券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大会总结
新闻动态 · 2003-01-28 00:00
返回[[image1]] 首先,宋敏教授发表了简单的讲话。他认为会议开的很成功,并感谢了大会的工作人员。接着,宋教授分别请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的领导作总结。以下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的总结。...
[[image1]] 首先,宋敏教授发表了简单的讲话。他认为会议开的很成功,并感谢了大会的工作人员。接着,宋教授分别请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的领导作总结。以下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的总结。
刚才大家讨论很热烈,并提出了很多问题。我想先对这些问题做一个回应,然后再作大会总结。我非常同意宋敏教授的观点,就是我们需要考虑一下怎样来度量“自生能力”这个概念。我和我的一些学生正在努力的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这个概念有点像“交易费用”的概念,都是看起来很容易,但是却不太好衡量。但是如果不能衡量的话,对理论的贡献就会很有限。这是在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的研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新概念。但是,具体怎样来做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我对“自生能力”的定义是很明确、很狭窄的。在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的预期利润率应该是零。如果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在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能够达到这个预期利润率,那么我们就说这个企业是具有自生能力的。否则,就说这个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没有企业家会对它进行投资,它要生存就必须依赖政府政策的扶持,所以说它没有自生能力。在做这个定义时,我特指企业生产产品的技术选择是否符合经济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当然还有很多因素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利润,这里我把它们忽略掉了。这是因为,二战之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想在经济上尽快的赶上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就在于它们有高科技的资本密集的产业。因此,这些发展中国家就会在政策上偏好某些产业和技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人和企业愿意投资这些产业。于是有些政府就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用政策来诱导民营企业向某一个产业投资,比如韩国。这个概念讲起来很容易,但是真要衡量起来确实不容易。我们还必须在正式的模型中把这个概念模型化,我想至少要是两部门的模型。但是两部门的增长模型也是不容易做的。这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我还想谈一下肖耿教授的想法。制度是重要的,我一向都认为制度是重要的。但是,制度的安排本身可能是内生的。有可能制度的安排是果而不是因,如果不消除“因”就想改变“果”,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国有企业改革是最明显的例子。开始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在于厂长经理没有自主权。所以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开始改革的时候就放权让利,实行承包制,企业利润留成。结果发现虽然厂长经理的自主权提高了,积极性也提高了,但是国家作为所有者,得到的利润分配却减少了。后来又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是产权界定不清楚,从而提出了所谓的现代公司制度的改革。最完善的应该是上市公司了,因为它有董事会、监事会,还有股民的监督。但实际上,大部分的上市公司在上市三到五年之后,跟没有上市的公司并没有多大的差别。由于时间不够,今天就不细讲了。
我一直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其实,我是最早把制度经济学引到国内的学者之一,也做了很多关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我和蔡眆、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实际上就是在分析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制度形成之后怎样对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产生影响。国内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教授对我们这本书的评价很高,但他最后说,很遗憾,林毅夫居然没有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式来进行分析。后来我搞清楚了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没有引科斯的话,也没有引诺斯的话,而是直接分析制度是怎样形成的。但我们习惯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就要讲产权,要讲科斯的理论。我没有讲这些,所以他认为我不是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式来分析的。但我认为,并不是说科斯的理论就叫做新制度经济学,也不是说诺斯的理论就叫做新制度经济学。所谓新制度经济学是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制度形成的原因和制度的影响。我觉得《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和我写的其他文章一样,都是遵循着这个原则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同意肖耿教授的看法,即制度是很重要的。但在中国现阶段,很多制度安排其实是内生的。尤其是改革之前那套我称之为三位一体的经济制度,包括宏观政策的扭曲,资源配置方面用计划取代市场以及在微观上国家对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进行了很多直接的干预。其实这些制度安排背后都有很多经济学的道理。是什么道理呢,就是政府想要发展一批在自由竞争开放的市场中我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能靠民间的投资,只有国家用计划经济的方法把它们建立起来。改革以后,把市场引进来了,把竞争引进来了,可是企业所在的行业同样是没有竞争力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政府同样要对企业进行保护。这就回答了张俊喜教授提出的为什么我国开放的时候老是先对外开放,而不愿对内开放。比如说银行业,在这两天的讨论中,大家也都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大力发展中小银行,这样才能促进符合我国比较优势,劳动力密集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既能解决就业问题,又能解决我国加入WTO之后面临的竞争的问题。但是政府关于民营银行的政策一直都非常保守。我想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因为现在的国有企业都在依赖四大国有银行吸纳的储蓄来维持。83年以前国家直接对企业财政拨款,之后“拨改贷”,转而用银行贷款了。但这样做第一要保证资金,第二要保证贷款的低价。如果允许很多民营银行进入,由于它们比较有效率,可以支付比较高的利息,那么很多储蓄就会转移到民营银行中去了。国有银行没有储蓄,就不能保证国有企业的生存了。为什么要发展股票市场呢?也是为了解决国有企业资金的问题,让企业除了银行之外,还有一个可以廉价获得资金的渠道。五一九讲话说国有企业要三年解困,当时朱总理是这么想的,如果国有企业的技术提高了,它们就会有竞争能力。而要提高技术需要资金,当时打算财政拿2000亿,外资进来2000亿,再从股票市场上筹集2000亿。可是98年之前的股票市场非常低迷,那怎么办呢?于是就把股票市场炒高,从而可以很容易的从股市上拿到2000亿。所以,很多事情都跟国有企业要继续生存需要资金有关。为什么开放QFII而不开放QDII呢?因为开放QFII之后会有外资进入我国的股市,从而推动我国股市上涨(尽管有很多理由,但这一个应该是主要的)。那为什么不开放QDII呢?道理很简单。如果这样的话,我国将有大量的资金流向国外,从而会影响到国有企业。我们采用渐进式改革,一部分有生命力的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企业发展的很快,但它们是在资金循环体系之外发展的。资金循环体系主要是为了保证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的生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有很多问题,包括金融问题、地区收入差距问题、就业问题等都没办法解决。
那应该怎样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呢?笼统的讲,就是要提高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我把国有企业分成了四个类型,第一类企业的产品是我国国防安全所需要的,我们不能从国外得到,或者即使能得到我们也不敢从国外得到的。任何国家都必须用财政来解决这些企业的资金问题。但这样的企业数量应该很小。第二类企业是资金密集型的,而且具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市场换资金的方式。要么到国外上市,直接利用国外的资金;要么跟外国公司合资,直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第三类企业也是资金密集型的,但它们的产品并没有很大的国内市场。这一类企业需要转产。我们的国有企业中有不少就是通过转产而具备了自生能力,如四川长虹。如果要转产,企业必须得有比较好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第四类企业并不具有这些条件,产品在国内有没有市场,只好破产。但是这样的企业大概也不多。这样就基本上能够解决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剩下的就是管理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改善管理,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就会产生比较好的效果。只有这样,产权、股票市场等才能够起作用。我一般不强调这个,并不是我认为这些不重要,而是我认为我们看到的制度的扭曲本身是内生的。如果不把外生的原因先消除掉,那么无论内生的果怎么变,都解决不了问题,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这就是我的想法。
以上一方面是总结我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是对大家评论的一些回复。我觉得这两天的会是非常高水平的。会议讨论的问题也是我国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有待解决的、也可能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这次会议准备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但是国内(包括香港)有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短时间内就收到了40篇论文。而且总的来讲,这些文章的质量是相当高的。开始的两个panel虽然没有文章,但是提出的问题也基本上涵盖了我们当前金融市场上的一些主要问题。我建议把这些文章整理成专集,我想它将会成为进一步推动我国金融改革和金融理论发展的一个很好的起点。这次会议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以及香港大学工商战略研究所合作的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作为中心主任,盼望着合作能够继续下去。我觉得中国的这些问题是我们作研究的一个土壤,作这些研究可以达到经济学家两个目标的统一。即“doing well”(可以取得学术成果及得到晋升)和“doing good”(我们的研究对社会是有贡献的)的统一。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目前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而金融市场改革是最棘手、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在这两天的讨论中,我发现有这么多的人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愿意花时间来研究。所以我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就可以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正如肖博士所说,现在是“世界看亚洲,亚洲看中国”,所以我们为中国做贡献,也就是为世界做贡献。好,谢谢。
宋敏:下面请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的院长陆教授来做总结。以下是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陆院长的总结。
我基本同意刚才林教授所说的内容。这次会议我们香港大学有十一二位同事参加,我想我可以代表我的同事对这次会议感到满意。我们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跟北京和其他地方的学者就这么重要的课题——中国金融改革——来交换意见。我们也特别感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朋友们在这次会议上给我们所做的安排。这次是我们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个很具体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我们也希望以后能继续下去。我们继续合作有一定的基础。首先,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我们说中国经济要和世界接轨,实际上中国经济学已经很早就与世界经济学接轨了。在这方面林教授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其实是功不可没的。严格来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自生能力”是非常强的。(笑)所以我们非常高兴能跟他们合作。其次,我们有共同的关怀。虽然我们在香港,但我们对中国内地的发展也有几个不同层面的关心。第一个层面是自然而然的,香港人就是中国人,很自然的要关心中国的发展。第二,现在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是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产生的很多问题,纯粹从学术观点来看也是很有趣的。第三,中国内地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对香港本身也有很直接的影响。不光香港回归之后是这样,其实多年以来一直是这样,不单是这五年,也不单二战之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影响香港经济的发展。现在的香港经济其实有一点“精神分裂”。香港在货币和金融上比较接近美国,而在实际经济方面,香港和内地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且越来越密切。总之,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关怀,这是我们以后合作的基础。同时我们两个地方又各自有自己的比较优势。我们的优势是跟外面接触的比较多一点,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优势是比较接近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希望以后还会有更多类似的有关中国经济和金融的研讨会。除此之外,还可以有其他形式的合作。总的来讲,能有机会来跟大家交换意见,我感到非常高兴。谢谢大家。
宋敏:谢谢陆教授,谢谢林教授。我刚才的感觉是双方的领导对我们这次会议的评价还是相当高的。同时我还有另外一个感觉,不知道对不对,是否我已经得到了一个尚方宝剑,就是将来我们还可以继续开会。我希望明年在同样的时间还可以开一个金融方面的研讨会,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支持我们。